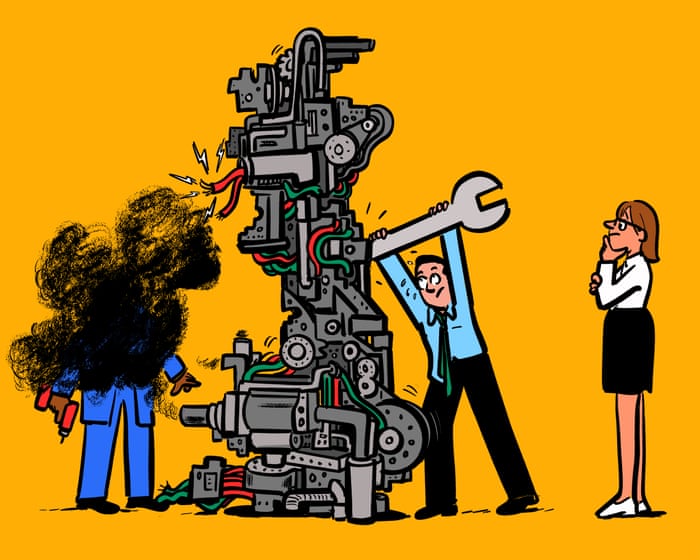我遇见克雷格时他才十三岁,流落街头。那时我还怀着一丝希望,以为他的生活能够好转。遗憾的是,我错了。
初次见到克雷格时,他还是个离家少年。他从当地儿童之家失踪,整日在诺丁汉市中心游荡。虽然只有13岁,这个金发少年却比同龄人高出一头,却始终未被当局发现。没有人寻找他,也没有人寻找聚集在市场广场的十几个孩子——他们大多从福利院逃出,有些逃学旷课,还有像克雷格的朋友米基这样根本不愿回家的孩子。12岁的马克自称从寄养家庭失踪数月,在街头度过了生日。这群孩子在巷弄里相拥而眠约一周,在彼此的陪伴中寻找慰藉。 克雷格负责安排寝具,从资深露宿者那里学来经验。他向我展示藏在垃圾桶后的纸板,语气不甚确信地说:"这样骨头不会受寒。"这就是他对流浪生活的初体验。 时值1998年,我正在诺丁汉拍摄第四频道纪录片系列《迷失生存指南》。英国正面临未成年失踪危机——儿童协会报告估计每年有10万儿童失踪。我们追踪拍摄克雷格这样在体制外求生的少年,记录他动荡不安的生活。表面看来,这个沉默观察街头戏剧的少年对周遭混乱无动于衷,无人知晓他内心的迷惘。 克雷格偶尔会乘四英里公交,回到1970年代建成的故居小区。某日同往时,他兴致勃勃向我介绍这个"庄园":少年们骑着不合身的自行车,运动鞋悬在电话线上摇晃。"扔着玩的,"他坦言,"这儿实在无聊。"虽如此说,归乡之喜溢于言表。 在他母亲窗明几净的家中,尘不染的摆件未泄露任何往事。克雷格解释房子已住满——姐姐带着婴儿在此居住,兄长则搬离另居。母亲为我沏茶,却对幼子无话可说。她称儿子是"噩梦",称其行为令她难以承受。在给予"最后机会"后,她将孩子送进福利院。无人知晓究竟有多少人曾真心尝试帮助他。 这次探访未持续太久。若克雷格曾在此拥有房间,如今也已痕迹全无。13岁的少年乘公交返回市区,开始思量今夜栖身何处。 纸板床铺的新鲜感消退后,克雷格开始寻找更隐蔽的容身之所。他曾从车站附近破败的空屋来电,名为乔克的男子允许他睡旧扶手椅。但此处终日喧闹,乔克的朋友们带着血迹斑斑的鼻子和阴晴不定的情绪随时造访。 天气尚可时,他尝试在森林游乐场露宿,又觉过于暴露。附近红灯区人流如织,寻芳客川流不息营造着不安氛围。车灯光影间,克雷格认出福利院的女孩在此谋生,更听闻少男在公厕卖身的传闻。这是90年代——被剥削的儿童仍会被起诉并贴上"雏妓"标签。几夜后,他重返市区。 警方不时会在城中发现克雷格...他被送至救助中心再遣返儿童之家。半心半意地抗议后,他任由自己被塞进警车。几小时后,他又会现身街头。福利院无人阻止他离开,也无人追问他的逃离。 "他在试图逃脱,"乔迪·杨近日告诉我,"逃亡会让你面临更糟的处境,但依然相信任何地方都比福利院好。"已超龄离开福利体系的乔迪18岁时海洛因成瘾,终日在中部银行取款机旁行乞。出人意料地,她成了克雷格等人的保护者,允许他们暂住在她与男友戴夫及杰克罗素犬彭妮合租的公寓。"我知道他们害怕,"她说,"想给他们个安全去处。" 若说有人理解克雷格的逃亡,非乔迪莫属——数年前她曾入住山毛榉之家,正是克雷格屡次逃离的那所福利院。两人对福利院时光闭口不谈,心有灵犀地任往事尘封。公寓曾短暂成为避风港:地板上铺着正经床垫,夜晚常共享杯面。深陷毒瘾的乔迪警告少年们远离海洛因。最重要的是,公寓里每个人都感到同病相怜——被本应守护他们的人辜负,他们必须相互照应。 拍摄临近尾声时,这短暂稳定土崩瓦解。乔迪与戴夫遭驱逐,小狗彭妮被带走,公寓门窗被封。已长高三十厘米的14岁克雷格再度无家可归。连警方都不再送他回福利院。在这个危险转折点,我冒险建议他探望母亲。经过尴尬开场,母亲勉强同意让他在沙发暂住。规则立下,承诺作出,备用羽绒被找出。但我未抱太大希望——局面迅速崩溃,很快克雷格来电告知再次启程。 18个月来,克雷格信任我们拍摄他的逃亡生活。突然,诺丁汉市议会介入,宣称对他负有责任并坚持我们无权拍摄。他们申请禁制令阻止纪录片播出。经过皇家法院数日煎熬的交叉质询,判决支持我们。克雷格有权讲述自己的故事,《迷失生存指南》于2000年4月播出,当时他年近十六。 我仍期盼境遇好转,但影片播出后的 year 里,警方开始因轻罪逮捕克雷格。不久他被送往青少年管教所。首次探监时,他用访客室的自动售货机为我买了咖啡。谈及想接受机修工培训,但说需要先有住处。他不知如何实现——此时他几近成年,已非住房优先保障对象。离院care者的统计数据对他不利。很快,他就能背诵自己的囚犯编号。 起初他仍在试探界限。19岁左右,他萌生假装持枪抢劫小超市的念头。受惊的收银员交出现金,他携款逃逸。但这不像克雷格的作风。次晨他主动投案。"我挥之不去那个画面,"后来他告诉朋友,"把那女人吓得半死,我无法承受。" 史蒂文·拉姆塞尔于2004年初次见他。"记得在陈旧阴暗的布里德韦尔警局与克雷格对坐,"这位讼务律师告诉我,"他是我最早代理的当事人之一。"若只看表面,你会见到商店扒手、麻烦制造者。确实他犯下诸多罪行,但都是轻罪——这是他唯一熟知的生活。克雷格避免入室行窃,却精通偷窃手机钱包。25岁时已是司法系统常客,据拉姆塞尔说,他几乎无法适应日常社会。"在外面的世界,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正常生活,"2017年克雷格从诺丁汉监狱来信写道,"总感到尴尬格格不入。这不是借口,但真心不知从何开始。" 年少时曾有人试图帮助。记得他少年模样的人允许他淋浴或借宿几晚,少数人甚至容他长住。但克雷格总会"报恩"——用赃物塞满冰箱,警察登门,耐心耗尽,他再次启程。"克雷格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人们常这么说。 此后十年间,我常不知他身陷囹圄或重获自由。而后会突然接到录音提示电话:"本次通话来自囚犯。所有通话将被录音并可能受到监控..."克雷格的声音随之响起,解释着逮捕、未执行令状、召回候审交织成的罗网。"你还好吗,帕姆?"他从不忘记问候。我尝试分享生活琐事,深知他难以想象我身处的世界。他爱听我的旅行见闻和家近况,也知道我总为听到他声音而庆幸。 他常请我寄送《迷失生存指南》的DVD副本。这部影片是他的骄傲,说是此生唯一真正完成的成就。他试图放给狱警和志愿者看,盼他们理解他的经历,盼有人能助他扭转人生。但工作人员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深究囚犯往事。"该给我拍续集纪录片,帕姆,"他常建议,"让人们看到真相,看到我的后来。"但电视行业风向已变。有位制片人说克雷格根本没有"电视脸"。 一次次出狱时,他总无处可去。怀揣善意离开,计划与缓刑监督官会面。但那些充满表格申请的约谈令人焦虑,且往往毫无结果。于是他找朋友借宿——对方出于好意收留。若他来电,我有时能听到背景音的混乱。"这儿挺好,"克雷格总这样保证,但局面总迅速崩溃。 记得他屡屡丢失微薄家当——遗留在旅舍或朋友住处。总有台"音质绝佳"的音响无法携带,总有双运动鞋被遗忘,尽管脚上那双已近乎垃圾。某个严冬,他在监狱间转移时丢失所有物品,从赫尔监狱释放时只穿着标准运动服。我致电监狱试图找人替他寻衣,照例无法接通。幸亏机敏体贴的牧师团队带着失物招领处的外套围巾在门口等候。 没人某天醒来就决定成为海洛因瘾君子...我确信这非克雷格所选,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较长刑期期间,他有时会参加戒毒计划暂时清醒。但监狱内容易获得毒品,这常成为他的应对方式。克雷格曾来信写道:"我逃回毒品怀抱,因为我知道如何当瘾君子。我知道该做什么如何表现,而在其他情境中我一无所知。事情变得太情绪化。就连去预约都会恐慌——无论是就业中心还是别的——我脑子里一片慌乱。出门在外时,感觉又回到了13岁。" 33岁时,克雷格已有170项犯罪记录,在外界的时间愈来愈短。"他已被体制化了,"拉姆塞尔告诉我。他历经司法体系太多次,任何支持都不足以带来真正改变。"本该有其他选择,但不存在,"拉姆塞尔说,"克雷格总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回到旋转木马上。"于是2018年春,诺丁汉监狱的大门再次为克雷格敞开。 随后数月,克雷格联系异常频繁。当时诺丁汉监狱是全英最恶劣的监狱之一,刚收到首席监狱监察官的紧急通知,实质上被置于特殊管控下。积压数年的紧张终于爆发,狱警与囚犯皆感不安。毒品——特别是危险合成大麻素"香料"——随手可得。18个月间,12名囚犯自尽。 "连入睡都逃不开烦恼,"克雷格在牢房里写道,"白天活着噩梦,睡着仍是噩梦。真不知还能否撑下去。脑子一团糟,日子越来越难熬。好想从自己这里获得解脱。"他的电话充满绝望,信件越写越长。若某日没有音讯,我便忧心不已。 牧师约翰·西尼在帮助克雷格度过刑期时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必须与克雷格共同坚持,"西尼常对我说。每周二克雷格都会申请离开囚室区前往监狱教堂,西尼带领的小型跨信仰团队在此提供倾诉空间。克雷格从未缺席,甚至开始写诗赞美所得的支持。 而后恍若微小奇迹:2019年初克雷格获释时,西尼设法在诺丁汉附近小镇伊尔克斯顿为他安排了教会关联房屋的房间。我乘火车探望时,他已在车站等候。告诉我他去了游泳馆,还到图书馆学习电脑使用。用长绳系着的钥匙打开合租房屋门,冰箱里有牛奶,他为我沏了茶。我们在阳光灿烂的后院度过平常午后,至今仍存着他眼中闪动希望微光的照片。 临别前他带我去做志愿者的教堂,在每日开放的快闪咖啡馆帮忙。年长的志愿者们正为茶饮分配器和装满饼干的塑料盒忙碌。当大家对"茶巾轮值表"困惑时,克雷格主动提出轮班。有位女士略显疑惑地递给他装满毛巾抹布的塑料袋。离开教堂大厅时,我还在担心他是否有洗衣机或是否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