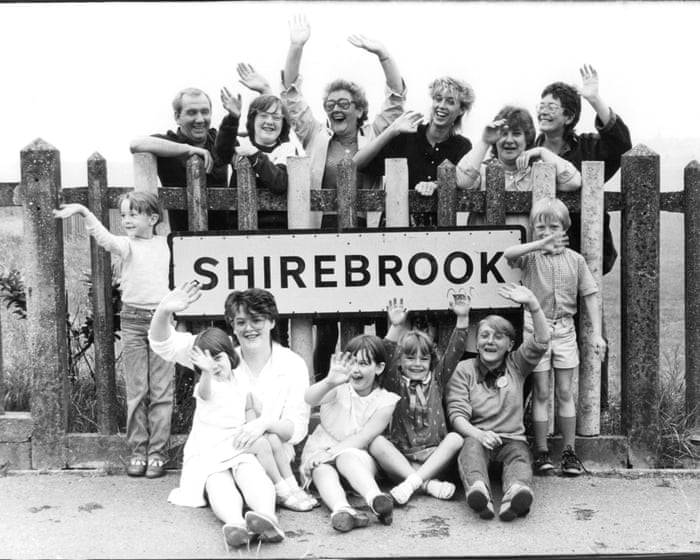"我现在必须做所有事":曾为战地医护人员的乌克兰剧作家
十八个月前,阿尔琳娜·萨纳茨卡还在乌克兰前线担任战地医护兵,甚至经历了巴赫穆特残酷战役,那时她几乎从未踏足过剧院。仅仅六个月后,她已准备在基辅出席自己的戏剧首演。如今38岁的萨纳茨卡创作了多部剧作,正逐渐成为乌克兰戏剧界最引人注目的声音之一。 这般急速转变对这位自幼热爱写作、却曾视剧作家如莎士比亚般遥不可及的女性而言堪称奇迹。她将快速崛起归因于战争。"我相信俄罗斯人可能在未来几年用无人机、火箭或街头暗杀夺走我的生命,"她说,"所以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在此刻此地完成所有事。" 她的处女作《军旅妈妈》从公开征选中脱颖而出,入选由剧作家马克西姆·库罗奇金(曾于2022年在卢甘斯克作战)联合发起的"退伍军人剧院计划"。该计划旨在让现役军人与退伍军人将战争经历搬上舞台,该剧最终在基辅左岸剧院成功上演。 这部剧作聚焦普通女性的军旅生活,涉及母职、军队性别歧视、破碎关系、心理挣扎与逃亡等官方战争叙事中常被忽视的议题。她坚持不刻意渲染积极情绪的直白写作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当获奖作品《平衡》在第聂伯罗上演时,这部描绘战地医护严酷现实的作品引来了当地神职人员与官员向剧院投诉。 "演出结束后,导演为剧中的粗话和写实手法道歉,"萨纳茨卡回忆道,"但这无济于事——剧院代表被传唤至市政府受到训斥,理由是剧本不够英雄主义且用语粗俗。" 然而观众们珍视她对前线生活的真实呈现。今夏《军旅妈妈》在基辅演出后,有观众感动落泪,演员们还参与了演后谈。一位丈夫在前线、父亲是退伍军人的女性特意感谢剧组揭示了战壕中的真实生活。 萨纳茨卡指出士兵们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作品折射出日常军旅生活。但剧中同样批判了对士兵处境一无所知的平民。在演后交流中,她常被问及是否憎恨平民。"每次我都保持沉默,"她表示,转而让更擅沟通的导演应对这类问题。 其最新作品《佩内洛普》灵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忠贞妻子,今夏在利沃夫的莱西亚·乌克兰卡剧院首演。该剧由七位女演员演绎,由斯维特兰娜·费德什娃执导,聚焦于等待亲人从战场归来的女性群体。"我本可以创作英雄主义故事粉饰太平,"谈及创作初衷时她说,"但我不愿让等待丈夫的女性在剧院看完童话后继续无望等待——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前,曾从事数年性工作(包括攻读心理学学位期间)的萨纳茨卡正以社工身份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支持暴力受害女性与药物成瘾者,同时倡导性工作者权益。 退役后她持续攻读博士学位,组织改善士兵权益的抗议活动,并参与援助伤兵及其家属的网络工作。目前她正在德国进行写作驻留,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在入选退伍军人剧院计划前,她坦言对戏剧领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莎士比亚是剧作家,仅此而已。"但担任战地医护期间,她常为部队筹款在社交媒体发布犀利动人的对话片段,正是这些文字促使友人鼓励她申请该计划。 尽管如此,她本人仍非戏剧爱好者。"我讨厌剧院,"她直言,"当然至今看过些有趣作品,但这绝非我消磨闲暇的首选。"事实上她的文学灵感源自小说家斯蒂芬·金:"好故事自然能征服舞台。" 另有一部题为《月经》的剧作将于年底在基辅莫洛迪剧院首演,探讨2022年战乱中性工作者的经历——这些故事在乌克兰几乎从未被公开讲述。 她近期完成的剧作《脂肪》在当下与1930年代间交错叙事,将现代乌克兰的饮食失调与1932-33年斯大林残酷粮食配额制造成夺去三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霍洛多摩尔)相联系。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以清晰自然的语气呈现关于这位乌克兰剧作家兼战地医护兵的常见问题解答 基础问题 1 "我必须立刻完成所有事"是谁? 这是娜塔莉亚·布洛克的笔名,这位乌克兰剧作家、编剧曾在前线担任战地医护兵 2 为何使用句子而非常规姓名作为名字? 这是艺术化笔名。"我必须立刻完成所有事"这句话凝聚着紧迫感与责任感,折射出其在战争经历中的强烈现实体验 3 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什么? 最具影响力的是剧作《女战地医护兵指南》,该作品基于亲身经历创作并在国际范围内上演 4 是否真正担任过战地医护兵? 是的,她曾在顿巴斯地区作为志愿战地医护兵,为士兵提供关键的前线医疗救护 关于其作品与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