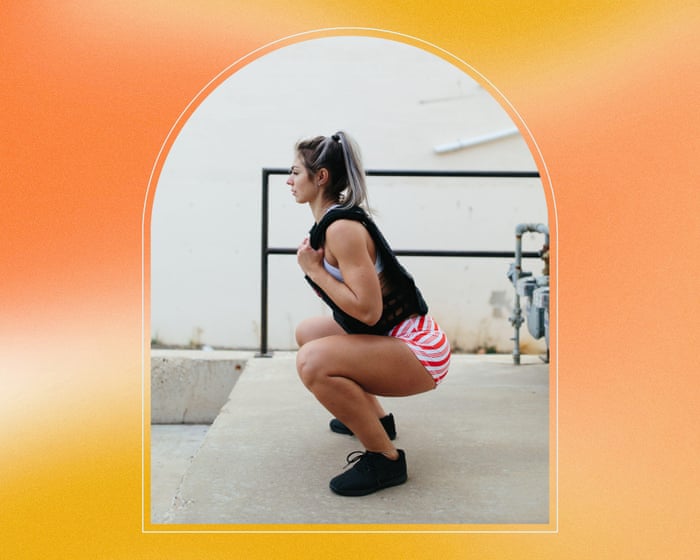当然不需要。没有必要进行“寄生虫排毒”。
去年八月,超模海蒂·克鲁姆透露,她和丈夫汤姆·考利茨正计划进行一次蠕虫和寄生虫排毒。她告诉《华尔街日报》:“我此刻Instagram推送的内容全是关于蠕虫和寄生虫的。”她还语带不祥地补充道:“不知道最后会排出什么东西来。” 也许你的社交媒体推送并没有充满关于蠕虫和寄生虫的帖子——如果是这样,恭喜你。但如果你在TikTok或Instagram上输入“寄生虫排毒”,就会看到大量所谓的专家在推销昂贵的草药补充剂,声称可以给身体排毒,清除有害的蠕虫和寄生虫。 一位自称“整体疗法妈妈”的TikTok用户建议,如果人们遇到“睡眠问题、肠道问题、减肥问题、情绪波动、皮肤问题”,就应该进行驱虫排毒。 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没有上述任何问题的人。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进行寄生虫排毒? “不!”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发言人卡罗琳·苏西在电子邮件中用大写字母写道。她强调,目前没有确凿的临床证据支持这些排毒方法。 理想情况下,医疗专业人士的强烈反对足以成为避免某件事的理由。但如果你仍然不相信,以下是关于寄生虫排毒你需要知道的信息,以及为什么你可能不需要这样做。 **什么是寄生虫?**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定义,寄生虫是生活在另一种生物体内、体表或与其共生的生物,它们“从宿主身上获取食物,或以牺牲宿主为代价”。例如绦虫、跳蚤,或者我大学毕业后住在父母家时的状态。 克利夫兰诊所人类营养中心的门诊营养师贝丝·切尔沃尼表示,人类通过多种方式感染寄生虫,包括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以及直接接触受感染的粪便。有些寄生虫,如钩虫,当人赤脚走在受污染的土壤上时也能穿透皮肤;而其他寄生虫则可能在不卫生的环境中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播。 弗吉尼亚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威廉·A·佩特里博士指出,在美国和英国,最常见的肠道寄生虫是贾第鞭毛虫病和隐孢子虫病。两者都是通过摄入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的。 寄生虫感染极为常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全球近25%的人口感染了蛔虫、鞭虫和钩虫等寄生虫。世卫组织称,这些感染往往集中在“最贫困、最弱势的社区”,那里的人们缺乏清洁水和卫生设施。 切尔沃尼表示:“在卫生条件良好的地方,肠道寄生虫感染较为少见。” **寄生虫感染的症状有哪些?** 切尔沃尼说,症状因寄生虫类型和宿主的健康状况而异。常见症状可能包括腹泻、恶心和/或呕吐、胃痛、食欲不振或饥饿感增加、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皮肤刺激、粪便中可见的蠕虫或虫卵,以及肛门或生殖器周围瘙痒。 **什么是“寄生虫排毒”?** 克鲁姆将她的排毒描述为涉及“所有这些草药”。社交媒体上宣传的大多数所谓疗法包括服用草药补充剂(如茴香、丁香、葡萄籽、艾草和白毛茛)、改变饮食习惯(如不吃加工食品或无麸质饮食),或两者结合。 **这有效吗?** 无效。 佩特里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寄生虫排毒方法有效或必要。”苏西补充说,如果有人在排毒后感觉好转,可能并不是因为清除了寄生虫,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摄入了更多营养丰富的食物。 家庭排毒也存在风险。苏西指出,补充剂不受监管,有些草药可能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高剂量时可能产生毒性。限制性饮食也可能导致营养缺乏。 **如何治疗寄生虫感染?** 切尔沃尼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感染了寄生虫,重要的是联系医疗专业人士,而不是尝试自行治疗。” 她解释说,感染可以通过粪便或血液检测来诊断,有时还需要通过内窥镜或结肠镜等影像学检查。切尔沃尼补充说,如果患者确实患有寄生虫感染,治疗方法取决于寄生虫的类型和感染的严重程度。通常,医生会开抗寄生虫药或抗生素,如果体重明显减轻,还可能提供补液和营养支持。 **寄生虫排毒对海蒂·克鲁姆有效吗?** 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无效。克鲁姆曾在万圣节装扮成蠕虫,她在11月告诉《人物》杂志:“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是关于寄生虫排毒的常见问题解答,旨在回答从基础到更详细的问题。 **寄生虫排毒常见问题** **初学者定义问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