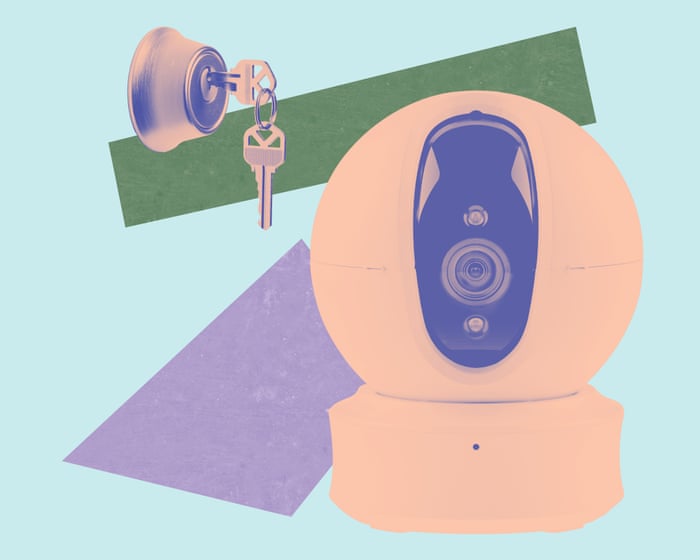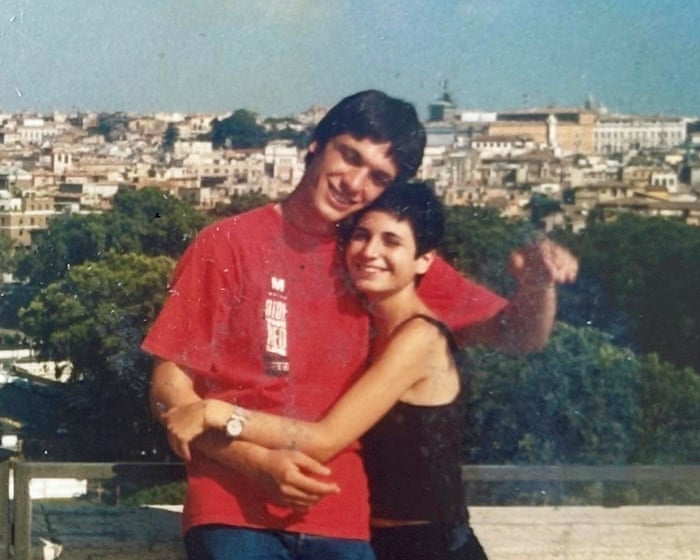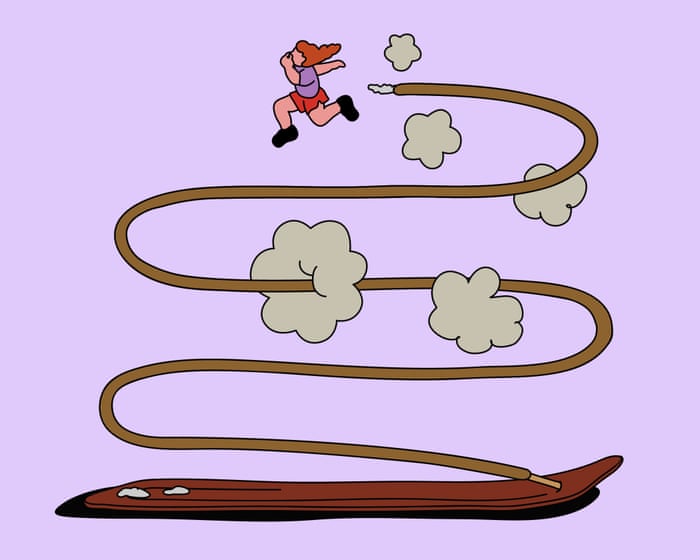在晚餐中寻找共识:“我们唯一达成一致的是都不喜欢改革派。”
塔克莎伊妮,40岁,伯明翰 职业:肿瘤科医生 投票记录:历史上她支持"任何非保守党的选择"。如今她的原则是"不投改革党或保守党"。 个人趣闻:她精通英语和泰米尔语,法语、德语和日语相当流利,还会些西班牙语,甚至"必要时"能搬出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麦穆娜,24岁,伯明翰 职业:医疗慈善机构教育项目助理 投票记录:身为保守党成员,但因鲍里斯·约翰逊和政党路线问题,最近两次大选都投给了工党。 个人趣闻:去年在哥本哈根酒吧巡游时,有人问她是否要参加下周的马拉松。她答:"才不是呢,我那会儿刚学会跑步!"结果今年五月她重返哥本哈根真跑完了全程。 开场白: 塔克莎伊妮:我本来有点紧张,部分原因是预期会见到强硬右派,但她完全不是。她特别友善。 麦穆娜:我们很快聊起国民医疗系统(NHS)罢工,听她的观点很有意思。 塔克莎伊妮:我吃了蟹肉吐司配美味虾汤,然后是鸡肉。甜点是草莓意式奶冻,还有超棒的无酒精调饮。 麦穆娜:我点了蘑菇冻、牛排、两杯橡木桶霞多丽和巧克力甜品。非常美味。 核心争议: 麦穆娜:我担心NHS难以留住医生,且过度依赖外国医生,这不利于培养本土人才。她说培训外国医生成本同样高昂,因为他们的资质可能不直接适用于英国体系。 塔克莎伊妮:她建议多培养英国人。但问题不仅是成本——许多医生职位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导致无人申请。不能强迫人接受这些岗位,所以向国际申请者开放。 麦穆娜:我的观点源于医学院朋友都想为更高薪酬跳槽。 塔克莎伊妮:我父亲移居此地时有近20年经验,却只能从初级医生做起。当时我5岁妹妹3岁,如今我们都成了医生。所以说,我们两个本土培养的医生能在这里,正是因为移民获得了那些岗位。 共享议题: 麦穆娜:我热衷健身,认为食品行业充满 predatory(掠夺性)。我们都认同体型不总代表健康。我问是否亚裔或黑人等族群在较低BMI时就会出现健康问题?她说是的,但基因也有影响。 塔克莎伊妮:我谈到人群差异——糖尿病与体重有关,也与种族相关;肥胖同理。我们尚未完全理解机理。但医生常对像我这样的患者说"你疼痛是因为胖,该减肥",结果却是其他病因。 餐后谈: 麦穆娜:辅助死亡违背我的宗教信仰,但我担心有人因自觉累赘而选择它。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何必急于求成?英国医学协会调查显示多数医生支持辅助死亡,但舒缓治疗和老年科医生除外。塔克莎伊妮提到她不从事这些专科,但怀疑有些医生担心辅助死亡可能分流舒缓治疗的资源。 塔克莎伊妮:作为患者,我需要时希望有这个选择。但作为医生,参与导致患者死亡非常艰难,即使那是他们的意愿。 共识收获: 麦穆娜:我很享受与塔克莎伊妮的交谈。能听到不同背景且更深入参与NHS的人的观点很棒。 塔克莎伊妮:我不完全清楚麦穆娜某些观点的逻辑——在这方面她显得年轻。但我们对改革党的共同反感拉近了距离。如果保守党里有更多她这样的人,或许能跟改革党好好较量一番! 本文补充报道由基蒂·德雷克完成。麦穆娜与塔克莎伊妮在伯明翰Pasture餐厅共进晚餐。想与不同立场者交流?请了解参与方式。 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