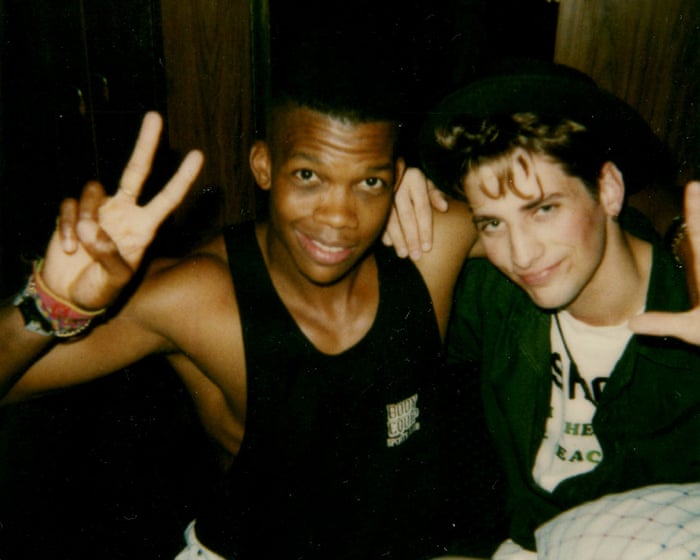在她遭枪击的一个月前,卡特里娜·布朗利产生了不祥预感。22岁的她在梦中看到曾虐待自己多年的前未婚夫——一名执法官员——试图杀害她,而自己幸存了下来。她自幼便常产生这类预感,后来逐渐将其视为上帝的指引。当她走向两人曾共同居住的房子时,脑中有个声音在恳求她不要回去。
那是1993年1月一个严寒的早晨。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布朗利带着两岁女儿乘出租车穿过纽约长岛的积雪,前往前未婚夫的住所。她七岁的大女儿当时正在朋友家玩耍。几周前布朗利已彻底离开未婚夫,带着女儿们躲藏在汽车旅馆。但近期他们通过电话,对方似乎接受了关系终结的事实,同意她取回个人物品。
"我只想拿回仅有的那点家当,"她说,"我当时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怀着孕还要照顾两个幼童,处境极其艰难。"
他放她进屋。安顿好女儿在卧室后,她走进主卧收拾衣物。房间仍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模样:米色地毯、白墙、整理好的床铺。但当她拉开抽屉,里面空空如也。心脏开始狂跳——难道前未婚夫设计骗她前来?
转身走进客厅,她看见他正用枪对准自己的腹部。三声枪响后,布朗利记得火药味弥漫,目睹自己隆起的孕肚"瞬间塌陷"。倒在沙发上的她惊愕地发现没有流血,竟仍挣扎着跑向卧室拨打911,但电话线已被切断。试图翻窗逃生时,发现窗户全被钉死。她以为对方会先杀害母女再自杀,奇迹的是女儿在隔壁始终安静无声。"我想他完全忘了孩子存在。"她回忆道。布朗利的尖叫声中意识到:"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从没有访客。这就是终局了。"
一个半小时内,她身中十枪:腹部三枪,手臂、臀部、髋部各一枪,阴道四枪。他还用木板猛击她的头部。"不想和我在一起?"她记得对方咆哮,"我满足了你所有要求,你却永远不知足!"
如同梦中装死求生,现实中她如法炮制,最终失去意识。
前未婚夫将她的躯体拖进浴缸。若非其表兄及时赶到,她必死无疑。这位表兄数小时前通过电话察觉他"情绪狂乱",发现血泊中的布朗利后立即驱车送医。
18岁初遇时,年长六岁的他开着好车,担任狱警工作,令她心生仰慕。布朗利由祖母抚养长大——生母16岁产女后便将新生儿遗弃医院。任图书管理员的祖母在丈夫离家后深陷酗酒困境,布朗利在回忆录中形容祖母是"遭命运亏待的好人",一位热爱圣诞、烘焙与灵魂美食的时髦女性。虽与另组家庭的生母保持联系,布朗利始终感受不到母爱。尽管祖母尽力照料,这个家庭始终充斥着混乱。
1970年代,布朗利与祖母、姨母同住在布鲁克林褐石宅邸。房东是住在楼下的毒贩兼皮条客,几乎夜夜举办派对——布朗利记得曾目睹桌上成堆的可卡因。在此期间她遭遇性侵。十岁时房东赌输房产,全家被迫迁往附近的布雷武特住宅区。
14岁因与年长少年发生关系怀孕,惊恐的她试图忽视孕肚,甚至滚下楼梯企图流产。祖母发现后由生母带至诊所,此时已怀孕27周无法堕胎。九年级辍学生下孩子后,生母试图送养甚至带走婴儿数月,但布朗利坚持抚养女儿。
17岁时生母因癌症去世。不久后通过姨母的男友,她结识了后来企图杀害她的男人。
暴力初现于她怀孕数月后。当表示想要堕胎时,他毁掉推荐信并实施殴打。目睹暴力的祖母却劝她继续这段关系,认为他能提供更好生活。
1989年圣诞节他求婚成功,布朗利从祖母家搬入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特他父母家的地下室,等待新房建成。尽管他对女儿不错,但布朗利形容共同生活如同与火药桶相伴。订婚数周后的1990年1月,争吵中他将她推下楼梯。剧烈腹痛中她呼叫救护车,警车也同时抵达。当她报告遭受袭击时,未婚夫"亮出警徽"与警察私下交谈。最终警车与救护车双双离去,由他送医后早产一个月生下二女儿。
1991年夫妇携新生儿搬入长岛住宅。布朗利期盼新开始,但殴打愈发频繁剧烈。远离亲友的孤立环境中,她感到深陷牢笼。
她三次向警方报案,但每次未婚夫出示警徽后警察便转身离开——即使她身上带伤。无路可逃时她曾逃回祖母家,却被他强行带回。1992年末,当他用椅子残片猛击其头部后,她终于彻底离开。此时她已与邻居秘密交往,这段健康关系让她体会到爱的模样,同时也发现自己怀上前未婚夫的四个月身孕。回首往事,布朗利说所有征兆都指向最终那场谋杀。
医院醒来时,一群妇女正为她祈祷,其中包括前未婚夫的表亲——她在康复初期提供重要支持。昏迷九天的布朗利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后,逐渐拼凑出事件全貌:由于她成功指认凶手并提供地址,前未婚夫已被逮捕。
失去意识前,女儿们已随搬往外州的前夫母亲生活。医生判定她存活无望。住院期间,后来成为挚友的地区助理检察官凯莉·赫尔佐格告知,她在昏迷前留下了临终证词——这段记忆已完全缺失。
病床上医生接连宣布噩耗:胎儿未能存活,永久丧失生育能力,余生无法行走。被告知存活已是奇迹时,她却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回忆录中写道,女儿们成为她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住院约三周后,她开始物理治疗。最初训练收效甚微,但坚持带来惊人进展,夏末时已能独立行走。在此期间她找到信仰接受洗礼。
出院后前夫母亲允许她暂住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特的老宅。但当她拒绝向法官谎称自残后,据称被婆婆驱逐。布朗利带着孩子搬入布朗克斯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等待保障性住房。回忆这段岁月她说:"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带着两个孩子,还失去一个。痛苦持续蔓延,但你得努力让一切显得正常。"
前未婚夫庭审定于1994年4月。布朗利一度拒绝作证,既想开启新生活,也认为司法系统会因他的执法身份从轻发落。但赫尔佐格坚持:"必要时候,我会像追野狗一样把你拖上证人席!"她最终同意出庭。
多年后通过CBS纪录片,布朗利得知辩护方曾向法官提交疑似婆婆伪造的撤诉信。卫报见过的信件副本声明她不会起诉,若被传唤将作有利被告的证词。
最终前未婚夫认罪。赫尔佐格请求25年至终身监禁,但法官采纳辩方"激情犯罪"论点,对无前科的狱警从轻判处5-15年。"我的心被彻底掏空,"布朗利感觉司法再次背弃了她。
随岁月流逝,母女迁居布鲁克林东弗拉特布什。她试图建立生活秩序,却在亲密关系中屡屡受挫——包括与囚犯和毒贩的交往。"那时我已伤痕累累...若从未见过健康关系,又如何能识别?"多年间她感到只是生存而非生活,"我将麻木常态化了,在无人知晓的深夜独自哭泣。"
27岁时为寻求人生意义与独立,她考入纽约警局交通学院,夜间攻读高中文凭,伴侣协助照顾孩子。获得警员考试机会后,她于2001年通过考核成为警官。
为何选择警职?她说要成为"好警察"。"若像我这样的人不主动填补警民隔阂,还有谁会做?"她特别期待推动执法同理心、消除种族定性、建立警民互敬。
布朗利在缉毒队与扫黄组的卧底工作中表现出色。她遇到的性工作者多数有着类似创伤背景,"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某种虐待或忽视。"
2009年开始的心理治疗开启漫长自我疗愈。"首次咨询时彻底崩溃,只想躲进治疗师的手提包。那可能是我人生首次感到安全。"随时间推移,她感受到内在蜕变:"我开始相信,只要持续追随光明,就能完全康复。"
作为警官家暴受害者,她绝非孤例。1990年代研究显示美国家暴警员比例是普通人群的2-4倍。她始终未向同事透露这段经历,担心被视为心理不适任。她也回避处理家暴案件,认为对受害者支持不足且刑罚过轻。
2017年动笔、今年出版的回忆录不时犀利批判纽约警局,尤其针对警员间互不举报的文化。"我亲眼见证警察如何构筑'蓝色沉默之墙'。"她主张对警员强制心理辅导:"执法人员现场目睹太多沉重,回家后还要扮演配偶、父母、照护者角色...他们需要宣泄渠道。"
结束扫黄组工作后,布朗利转入社区事务部——她视为终极"好警察"岗位。她为高风险少女创立"未来淑女"导师计划,指导她们建立自信并识别虐待信号。"这能帮到少年时的我:即便不得不回到困境,你仍能带着应对工具离开。"后来她加入白思豪市长的安保团队,成为首批担任此职的非裔女性。
2021年完成20年警职退休时,她是一级侦探。不久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报道刊发后接到匿名电话。对方自称前警员,怀疑当年正是那个目睹她伤痕却因前未婚夫出示警徽而离开的警察。"他说:'当时我在那个分局,做过类似的事。如果是我,很抱歉。'随即挂断。"
若对方未挂电话她想问:"既然看到我眼圈发黑,为何不施援?若受害者是你女儿或爱人,你当如何?"她强调本可成为阻止谋杀的关键。
前夫服刑十年后获释。她努力练习原谅:"曾充满愤怒与痛苦,但不愿被这些情绪定义。我深信宽恕的力量——不为对方,而为自身与身边人。"释后唯一共处是出席其母葬礼,两人未交谈。
现年55岁的她致力于倡导、辅导与导师工作。沉默数十年后,如今公开探讨家暴议题,包括向执法团体演讲。她推动纽约立法禁止家暴定罪者持枪:"若能让施暴者远离枪支,家暴命案可减半。"同时致力建立家暴登记系统,供民众查询伴侣相关定罪记录。还主张对家暴者强制康复训练:"若只治标,症状必将复发。"
年底起她将探访联邦监狱,为家暴与其他暴力犯罪者提供辅导。
"家暴并非源于某人自认'我是施暴者',"她反思,"往往源自自身经历与成长环境。与受虐者交流时,我能与之共鸣。"在等待立法改革时视此为契机:"若无法促使国会与政府行动,我便自己踏出第一步,期待他们跟随。"
如今出差之余,她在纽约与南部住宅间往返。每日步行3.5英里保持活力,需要时持续接受治疗。宗教信仰成为人生指引。"这道伤痕永难愈合——但我已学会与之共存,"她说。
今年回忆录出版拉近了些亲属距离,他们阅读后才真正理解她的遭遇,有人为未能察觉端倪致歉。她毫无怨怼。35岁与40岁的女儿们尚未阅读此书:"待她们准备好自会读,我不愿触发孩子的创伤。"与前夫表兄仍保持亲密联系——这位救命恩人当年将她浴血送医。
尽管聚焦未来,1993年1月那个清晨始终萦绕心头。"没有一天不想起,但我已学会接受这就是人生,如何回应才至关重要。我抓了一手烂牌,但最终赢得了牌局。"
卡特里娜·布朗利回忆录《蓝调降临:我的生存与纽约警局崛起之路》现已出版(Akashic出版社,26.99英镑)。英国家暴求助热线0808 2000 247,或访问Women's Aid;美国家暴热线1-800-799-SAFE(7233);澳大利亚全国家庭暴力辅导服务1800 737 732;更多国际求助热线可见www.befrienders.org。
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您提供的情景,以下是清晰直接的问题解答列表
总体性 动机类问题
问:经历了如此遭遇后,您为何还要加入警队?
答:这段经历让我对暴力与受害者有着独特理解。我希望能运用这种视角保护他人,防止类似悲剧重演。
问:卧底警员具体从事什么工作?
答:卧底警员通过虚构身份潜入犯罪组织,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内部收集证据、协助构建案件。
问:重返危险环境难道不令您恐惧吗?
答:当然恐惧。但这种恐惧有所不同——这是带着阻止犯罪目标的专注式恐惧,而非受害者式的无助恐惧。
流程 培训类问题
问:重伤后您如何达到警员录用标准?
答:需要通过大量物理治疗才能通过严苛的部门体能与医学检测,这是个漫长艰难的康复过程。
问:您的个人经历对申请是助力还是阻碍?
答:这是双刃剑。警局关注我的身心状态,但也将我的特殊动机和对暴力犯罪的深刻理解视为潜在优势。
问:卧底培训与常规警训有何不同?
答:是的。警校毕业后,卧底警员需接受专业训练,包括构建掩护身份、识破欺骗、高危压力管理及高级监控技巧。
个人 心理类问题
问:您如何应对工作的心理压力?
答:这是持续挑战。我极度依赖警局提供的可信赖治疗师,以及极少数理解压力的同僚组成的保密支持网络。
问:卧底工作中是否需要与类似您前夫的人接触?
答:不幸的是需要。我经常接触施暴者,过往经历有助于识别行为模式,并能在任务中转化为优势。
问:您如何在保持伪装时不迷失真实自我?
答: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我设立严格界限,下班后通过解压仪式重新连接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