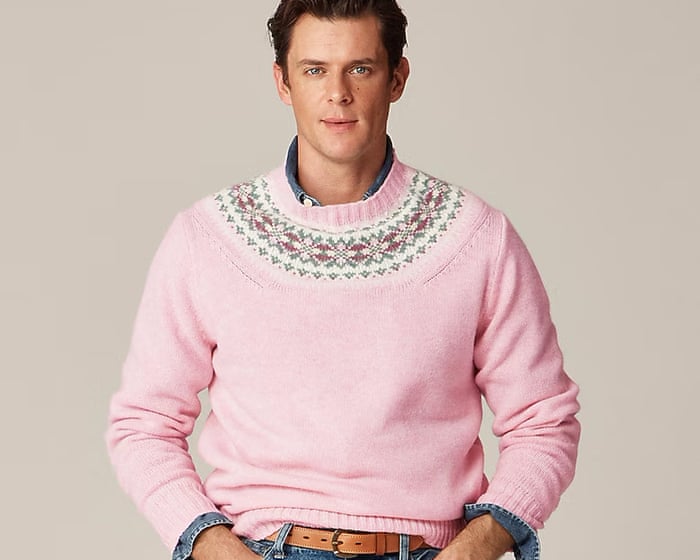当艾莉森·斯通纳九岁时,某电视节目的服装助理注意到这位童星腿上的深色汗毛,告诉她这样"很脏,不够淑女",并要求她剃除毛发后才能穿短裤出镜。"我开始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独立于我之外的存在——需要被控制、修正、塑造成符合任何既定标准的东西,"斯通纳坦言,"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娱乐圈极端苛刻的审美标准。"
这对九岁孩童而言是沉重负担,但彼时斯通纳已出道数年。她不仅是迪士尼的常驻演员,还参演过《儿女一箩筐》等电影,早已习惯听从成人指令。进入青春期后,这种顺从演变为极端运动习惯和进食障碍,最终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
后来,使用they/them代词的斯通纳转向福音派基督教寻求人生答案。在教会朋友"驱除同性恋恶魔"的劝说下,她接受了性向矫正治疗。直至32岁,斯通纳终于接纳自我,以酷儿身份出柜,并成为心理健康从业者与倡导者。在Zoom专访中回顾童星经历时,她感叹:"我从未有机会与自己的身心建立可信赖的连接。"
在回忆录《历经万难勉强正常》中,斯哥纳详述了童星生涯如何导致畸形人生:既要承载超高期望又要承受残酷拒绝,在其他孩子还没读完小学的年纪就面临"失败者"的审判。即便有幸获得影视角色,孩童也会被抛入要求专业度、随时酝酿情绪、必须长成魅力青少年的成人世界。这个体系奖励"适应性强"和"易于合作"——无论是容忍允许超时工作的法律漏洞,还是扭曲自我迎合行业期待。于斯通纳而言,这包括被要求防晒以免皮肤"变得太黑"。
童星的成功维系着周围成年人(父母、经纪人及雇佣团队)的生计。此外还要应对跟踪狂与死亡威胁——有次团队险些让斯通纳去见冒充绝症粉丝的绑匪。她与母亲关系亲密却紧张:斯通纳写道母亲过度沉迷于孩子的成功:"只要我闪耀,她就闪耀。"
斯通纳将童星之路称为"从蹒跚学步到人生脱轨的流水线"。通过著作,她"旨在用信息赋能而非问责个人。当我们认知提升,就能做出更优选择,尤其关乎儿童福祉"。她强调孩童根本不可能对职业演员生涯做出知情选择:"我严重怀疑将表演爱好商业化是否出自本心。"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长大的斯通纳自幼热爱表演,曾为学前班的宠物笼摆出半圆形剧场表演《油脂》歌舞。被发掘凯蒂·霍姆斯的星探相中后,她被打上"天赋异禀"的标签。"许多善意成人只想支持看似有天赋的孩子。若能重来,我会强烈建议以非商业化方式探索创造力。"艺术本质是美好的人性表达,但企业掌控姓名与形象则截然不同。由于成人管理不善,多年工作的斯通纳最终身无分文,尽管她曾以为自己拥有百万资产。
六岁时斯通纳开始参加选秀比赛,后与母亲移居洛杉矶承受无休止试镜与表演课。在某次课程中,她被鼓励调用真实痛苦——想象再见不到离婚后疏远的父亲。多年来她的身体开始抗拒这种深度脆弱,反而形成情感屏蔽的麻木状态,后被诊断为述情障碍。她认为这是无数试镜中自我创伤的后果,包括试镜绝症患儿角色或经历模拟枪战——却因"表现良好"受赞扬。"七岁孩童因演绎痛苦恐怖获奖励,这种体验何其荒诞。"
斯通纳曾成功参演三支Missy ElliottMV及《摇滚夏令营》《舞出我人生》等影视作品,但也经历无数落选。"当你自己成为产品,拒绝会内化成对自尊的蚕食。即使被选中,价值仍维系于外部认可,永远无法建立核心自我认同。"十二岁时她原本有望主演剧集,但机会因《汉娜·蒙塔娜》的横空出世而消散。面对黛米·洛瓦托等同龄人的光环,她"用否认伤害来应对,恐惧自我怀疑与嫉妒,沉溺于毒性积极主义"。
八岁起斯通纳就处于"永久表演模式",从未体验正常童年。在成人与镜头凝视下经历青春期尤为残酷,"对年轻女性身体突然出现性化表演的要求实在荒诞"。十三四岁时与成年选角导演独处一室并知悉需要"诱惑他们"堪称恐怖经历。
诸多"第一次"都发生在镜头前:排练《小查与寇弟的顶级生活》时亲吻主演兄弟,《儿女一箩筐2》中经历首次"约会"。她不得不谷歌查询应该展现何种情绪,"如同观察标本的科学家"。青少年时期她沉迷严苛运动与热量控制,极端节食导致停经。17岁时,十年顺从后终于求助。
因迫近的"童星失效期限",她曾被劝阻接受康复治疗。但最终在治疗中心首次体验规律生活,接触与利益无关的成年人。康复三个月后重返好莱坞时,她已开始寻找圈外人生。25岁时运营YouTube频道、研读心理健康、创作音乐。2018年通过《Teen Vogue》出柜导致失去儿童节目工作。
后来她创办《亲爱的好莱坞》播客探讨童星生态,在其中公开谈及二十多岁时遭遇的性侵。虽非童星时期发生,但这种体验令人悚然熟悉,促使她重新审视童年遭遇——无论是工作人员伸手入衣别麦克风,还是高管评论青春期身体发育。"成长过程中我似乎从未真正理解'拒绝'的意味,尽管有太多本该说不的时刻。"
如今她致力为幸存者发声,继续以公众人物身份推动社会变革,尽管常渴望匿名。她在片场担任心理健康协调员,为年轻演员开发工具包,希望业界能像重视亲密戏协调那样关注演员心理,尤其童星群体。她仍为《飞哥与小佛》等作品配音,已为回忆录引发的行业反弹做好应急准备。
历经贫富起伏,斯通纳看透好莱坞推崇的成功幻象:"18岁时当旁人刚入职,我已尝遍成功滋味,发现它们索然无味。"错过正常童年的她通过治疗与心理健康工作重建自我,写书过程让她与疏离十五年的父亲重逢,得知对方曾为监护权多年抗争。
"书中这些部分最具情感冲击且尚未化解,"斯通纳表示。与母亲的关系则是"不愿触碰的微妙领域"。通过写作,她终于超越Missy ElliottMV里的小女孩或迪士尼童星身份理解自我:"这给了我某种摆脱过去的自由。"
艾莉森·斯通纳所著《历经万难勉强正常》由潘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22英镑)。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是关于艾莉森·斯通纳经历的常见问题解答,内容简洁清晰,语气自然
**基础问题**
**问:艾莉森·斯通纳是谁?**
答:她是以童星身份成名的演员、舞者兼歌手,曾出演《儿女一箩筐》《舞出我人生》等电影,以及迪士尼频道《摇滚夏令营》《小查与寇弟的顶级生活》等作品。
**问:童年被性化意味着什么?**
答:指业界人士和公众在她未成年时就以性化视角看待她,包括不当评论、强调身体的服装设计及镜头聚焦,而非关注其艺术才华。
**问:她遭遇过怎样的跟踪骚扰?**
答:包括狂热粉丝非法入侵住宅、发送威胁信息等恶性事件,致使她与家人长期生活在安全威胁中。
**问:为何会饮食失调?她不算成功吗?**
答:节食源于好莱坞对极端瘦削体型的畸形要求——为符合行业标准被迫极端节食,而非物质匮乏所致。
**深度问题**
**问:这些经历如何影响其心理健康?**
答:导致严重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及身份认同撕裂。她曾坦言感觉自己活在割裂的多重人生中,难以剥离明星光环认知自我。
**问:她采取了哪些具体康复措施?**
答:包括强化心理治疗、暂退演艺圈完成学业与个人成长、重建与食物及身体的健康关系,并积极推动行业改革。
**问:当时业界可有人提供保护?**
答:她指出本应保护童星的体系普遍失效——环境更注重产出与利润而非儿童福祉,导致多数人只能默默承受。
**问:她现从事何种工作?**
答:除持续参与《飞哥与小佛》等配音工作外,更致力于担任片场心理健康协调员,为年轻演员构建心理支持体系,并通过写作与公众倡议推动行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