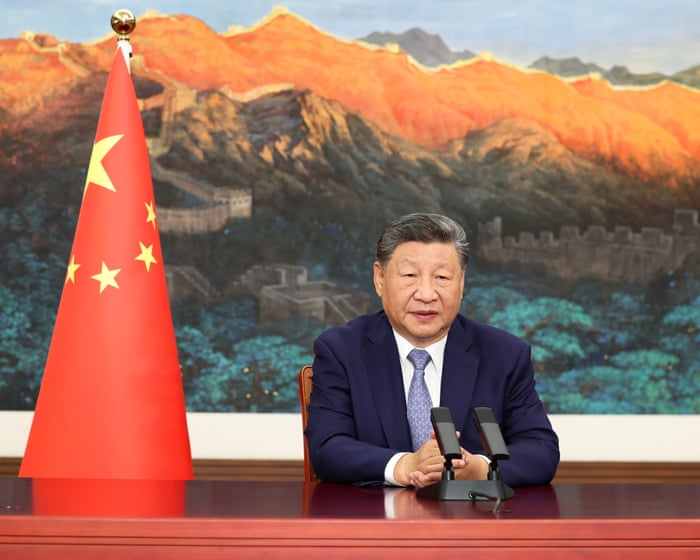直到上周四希顿公园犹太教堂遭遇可怕袭击之前,我从未真正意识到克拉姆萨尔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这个曼彻斯特北部的小社区仅有1.2平方英里,居住着1.8万居民。九岁那年我重病时,首先被送往的就是克拉姆萨尔医院;两年后我重返的特殊学校是克拉姆萨尔露天学校;而我所去的犹太教堂正是海厄·克拉姆萨尔会堂。
多年来,我或是将克拉姆萨尔视为理所当然,或是对它嗤之以鼻。这里承载着我最痛苦的记忆——重病缠身,以及我最抵触的生活部分——宗教信仰。我更愿谈论两英里外的奇坦希尔,那里似乎更酷更世俗,尽管两地常融为一体。讽刺而愚蠢的是,我当年竟觉得奇坦希尔更具危险魅力。
我离开曼彻斯特前往利兹读大学,数十年前又移居伦敦。父母始终住在布劳顿公园——一个距离他们成长地不足一英里的中产犹太社区。于我而言,这里沉闷闭塞。妹妹与我搬离后,他们换购了几条街外的小屋。近二十年前父亲离世,母亲始终守在她那条死胡同的小屋里。
很长一段时间,我厌恶探访。这里令人窒息,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交氛围。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坚守。尽管深爱着她,我却对她的社区抱持势利眼光,认为她值得更广阔的天地。她如同离水之鱼——一个恪守教规却本质世俗的犹太人(若这不矛盾的话),生活在哈西德派主导的社区。数十年间,这片区域愈发虔诚,用犹太人的话说就是"愈发遵奉教规"。
但当年的我何尝懂得狭小天地的真谛?在母亲晚年,我越来越多时间停留在她的住所,相伴或独处。她因病住院时,我常驻守于此探视;她返家休养时,我为亲近她而留宿。渐渐地,我爱上了这栋房屋与社区——或者说多元社区。在我离乡期间,越来越多穆斯林迁入克拉姆萨尔与奇坦希尔。他们并未取代犹太人,而是基本各自过着相安无事的生活。不仅是不同宗教共存,信仰实践程度也各异:极端正统派、正统派与世俗派犹太人比邻而居,穆斯林群体亦是如此,宛若彩虹中的彩虹。
克拉姆萨尔的1.8万居民中,近万是穆斯林,千人是犹太人,四千是基督徒。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犹太人口占比0.5%,穆斯林占比6.5%。这意味着克拉姆萨尔的犹太与穆斯林人口均为全国平均值的十倍。除4600名出生在中东与亚洲的居民(约占25%)外,还有逾千居民来自非洲。富裕区域与全国最贫困地带仅咫尺之遥。
母亲旧居五分钟路程外有家特易购超市。它如此庞大,我从未见过能迎合如此多文化需求的超市。母亲曾疑惑为何我总在此流连或在奇舍姆山徘徊。我告诉她这景象令人振奋——各阶层、宗教与种族的人们在同一片灰天下生活。我为此深深着迷,终于迟来地领悟:这个我曾斥为狭隘之地,实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熔炉之一。恐怖袭击五天后,它依然是。
当政客、宗教领袖与民粹记者试图在克拉姆萨尔撒播分裂——声称袭击是英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必然结果,或是对加沙种族灭绝抗议镇压不力,或是疏于犹太教堂安保的恶果——我们必须牢记:这场骇人袭击是特例。这是单人罪行(尽管有涉案者被捕),绝非某些人渲染的社群战争。
克拉姆萨尔过去是,现在仍是社区典范。这个郊区犹如微型和平的"两国方案",刚刚遭受了可怕却暂时的挫折。
对克拉姆萨尔及全球的犹太人与穆斯林而言,这是令人恐惧的时刻。2017年曼彻斯特体育馆恐袭后,这座城市以"反抗蜂群"的姿态展现出人性光辉。当时爱显然战胜了仇恨,如今克拉姆萨尔必须再次见证这样的胜利。
本文作者西蒙·哈滕斯通系《卫报》特稿作家。
(以下为技术性内容,按原文结构处理)
常见问题解答
基于您分享的情感,以下是清晰自然且实用的常见问题列表:
普遍理解与情感
1 为何总是在悲剧后才懂得珍惜某个地方?
这是常见的人类体验。我们常对熟悉的事物习以为常。创伤事件会打破这种常态,让我们敏锐意识到可能失去的东西,从而加深对其珍视。
2 为何危机会让人更团结?
共同的威胁或悲剧常能消弭个体差异。人们为相互支持、慰藉与力量而凝聚,在面对共同逆境时形成强大的社区意识与集体目标。
3 袭击后对故乡产生更强烈依恋是否正常?
完全正常。袭击为所有同乡创造了共同的情感体验。这种集体的悲伤、恐惧与韧性铸就的纽带比以往更深刻。
应对与个人行动
4 如何应对当前的悲伤与恐惧?
承认自身感受至关重要。与亲友或心理健康专家交谈。参与社区纪念活动或支持团体也能提供慰藉与团结感。
5 个人如何维护当前的团结?
细微举动亦有深意:关心邻里、支持本地商户、参与社区活动、分享故乡积极故事与回忆。主动选择善意能巩固团结。
6 我已移居外地但深受影响,如何远程助力?
可向经核实的本地救济基金捐款、联系当地亲友提供支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准确信息及城镇韧性的积极讯息。
社区与未来
7 社区如何主动维持这份团结?
可建立永久纪念物、创设聚焦团结与纪念的年度活动、组建保持人际联结的长期支持网络或邻里守望小组。
8 其他城镇在悲剧后维持团结的案例有哪些?
常见做法包括创建社区花园、以遇难者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启动象征韧性的公共艺术项目。这些都会成为集体力量与相互承诺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