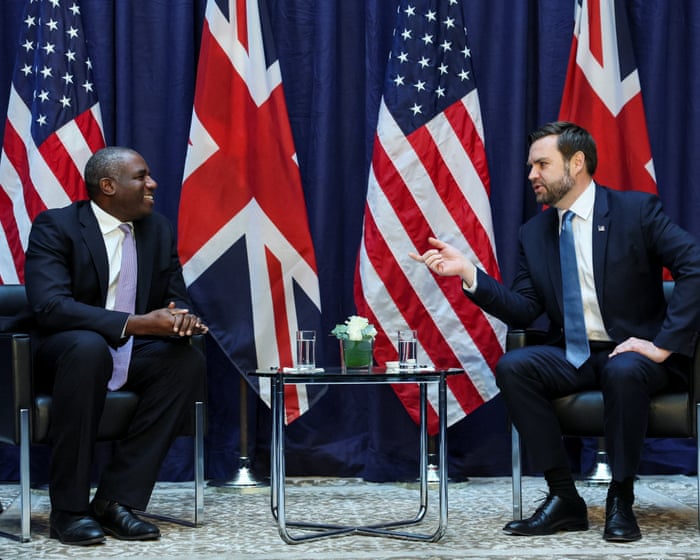有一幅画我时常想起——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60年的杰作《分娩圣母》,现藏于托斯卡纳蒙特奇小镇的博物馆。画中圣母玛利亚身怀六甲,两侧天使侍立。几个世纪以来,当地妇女将其奉为生育守护神。二战期间,她们甚至挺身对抗疑似纳粹的窃画者;1954年,当这幅画将被迁往佛罗伦萨时,她们躺在街道上用身体阻挡运输车辆。
昨日漫步国家肖像美术馆的珍妮·萨维尔个展,目睹文艺复兴艺术如何塑造她的创作时,我又想起了那些蒙特奇妇女。萨维尔对古典大师的痴迷始于童年——多亏有位艺术史学家叔叔带她游历威尼斯。这种影响在她描绘母性的作品中最为明显:那些她与子女相处的粗粝而有力的画像,分明流淌着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血脉。炭笔与粉彩作品《哀悼I》正是她深入研究米开朗基罗《卸下圣体》后的结晶。
为避免陷入艺术史术语的泥沼,让我们回到蒙特奇那些抗议的妇女。二十出头的我无法理解,怎会有人为文艺复兴画作甘愿卧街阻拦。那时宗教艺术总让我无动于衷——或许因我成长于非宗教环境。于我而言,那些不过是僵硬的圣婴像与跪拜人群。我明白其历史意义(透视法的诞生!),也认真研习过提香与米开朗基罗,甚至通过关于达·芬奇的口试。但若任选,我永远更爱抽象派与当代艺术——罗斯科或琼·米切尔的作品总能直击我心,这是文艺复兴绘画从未做到的。
我深知问题在我——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某些艺术特有的神秘火花、那种直击心灵的震颤,总与我绝缘。多年后站在萨维尔的母与子系列前,我顿悟这种隔阂不仅关乎宗教,更关乎生命体验。二十三岁经历生死劫难后,我的审美转向巴洛克风格(或许矫情,但创伤常通过艺术重塑我们——权当这是我的死亡金属阶段)。我曾拽着当时的男友遍访罗马教堂追寻卡拉瓦乔;在乌菲兹美术馆凝视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的《朱迪斯斩杀荷罗孚尼》时,我感受到了她的暴怒。
在萨维尔描绘叙利亚儿童的《阿勒颇哀悼》前,我几乎落泪。
年轻时,真挚的情感总让我羞赧难当,于是像多数二十来岁的人那样,我用玩世不恭掩饰天真。但随着岁月流逝,当生命遭遇重创,深刻共情不再令人窘迫。那时我刻意回避某些体验的情感重量——不仅是死亡,还有所有与母性相关的内容。我不愿触碰这些领域。
直到开始考虑生育时,报喜图突然吸引了我——就是天使加百列告知玛利亚将怀孕的场景。抛开童贞女怀孕的信仰,这些画作意外地触动了我。捕捉那种"意识到生命即将天翻地覆"的瞬间,突然变得无比迷人。当我自己验孕棒显示两道杠时,这种魅力更强烈了。
儿时临摹弗拉·安杰利科《圣母领报》时,我只画了天使,完全忽略了玛利亚。但多年后成年站在佛罗伦萨的原作前,我眼中只剩她脸上的神情。亲见艺术品确有不同,但我怀疑荷尔蒙也在起作用。
今夏,一位密友意外怀孕——快得让她和我当初一样震惊。我发给她那幅画,开玩笑说玛利亚"看起来快吐了"。或许在拥抱真诚方面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绝不会用现在的自己交换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版本。我宁愿做那个刚生产完就站在拉斐尔圣母像前泪流满面的女人——无论多难为情。
在珍妮·萨维尔的《阿勒颇》前,那些在以色列暴力中失去孩子的加沙母亲们的悲恸似乎都凝聚在画布上。我突然明白,蒙特奇的妇女们守护的不仅是艺术杰作——在她们眼中,更是在守护彼此与后代。
允许自己被艺术触动,也意味着向他人之痛敞开胸怀——甚至甘愿为其冒险。换句话说,随时准备躺卧街头。
(文末作者介绍及FAQ部分保留核心信息,按中文阅读习惯调整表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