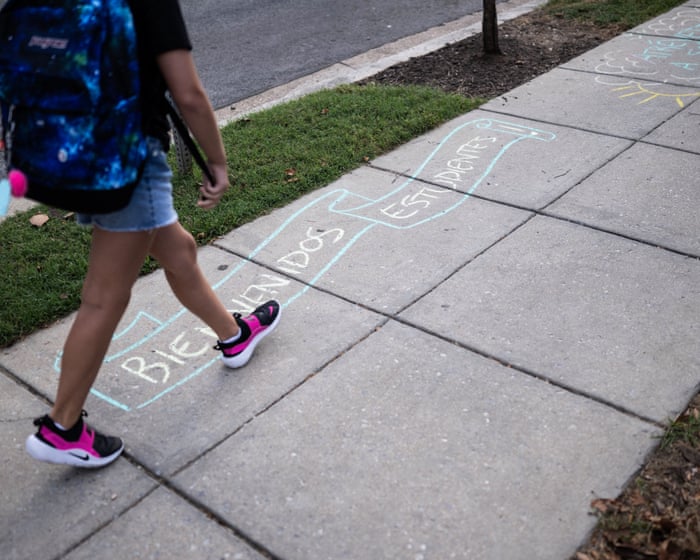我一向不擅长寒暄。往好了说,我觉得这种对话无聊;往坏了说,它让我焦虑。既然我自己能看见下雨,同事为何要特意指出?面对邮递员"今天过得如何"的问候,我怎么可能用三言两语回答清楚?
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些年,人际交往至关重要。聊起作家、印数或营销预算时我游刃有余,但若被问及如何赴约或停车位置这类话题,我顿时兴致索然。可偏偏这些才是主流对话。当他人谈笑风生时,我总感到拘谨而格格不入。
每次社交都像一场不及格的考试。我不懂寒暄的规则——该持续多久?该坦诚还是风趣?担心自己的回应不是乏味就是过度热烈,提问时总像在审讯对方。
成为自由职业者后,我像演员背台词般练习寒暄,努力展现从容自信。渐渐我习惯了这种表演,接受这种不适是成人世界的必修课。
直到封锁期来临。两年间我不再需要表演,当所有人都更脆弱时,对话反而更深刻真实。我很少与陌生人交谈,甚至不用穿裤子!
但重启社交后,重回谈论交通天气的日子犹如心理酷刑。我的社交技能早已生锈,长期佩戴口罩后,连戴上社交面具的技巧都已遗忘。
今年五月在朋友画展上,一切迎来转机。受韦恩·戴尔"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所见之物随之改变"的启发,我决定打破厌恶的社交模板,创建新范式。
遇到自由摄影师时,我首问:"你是什么星座?"她眨眨眼,惊喜答道:"水瓶座。"我们畅聊十分钟。接着我问下个人关于美术老师的往事。那晚我收获了数场愉悦对话。
趁着五月剩余27天,我继续实验。规则很简单:礼貌避开健康天气出行孩子成绩等话题,引入真正关心的事物。
当咖啡师问及如何享受阳光时,我转向:"喜欢春天,但更爱秋天,你呢?"在作家活动里,听到有人提起孩子放假,我便问对方当年最爱的学科。
结果出人意料。多数人不仅配合,还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原来不止我觉着寒暄尴尬做作。对话变得不可预测且真实起来:我听闻酒保的变装表演副业,毕业生的养蜂热情,心理护士创作的小说。
当然也有尴尬时刻。有人不解地看我一眼便离开,少数人充满戒备。但我并未在意——大多数人欢迎这种改变。
随着实验临近尾声,我意识到寒暄尽管恼人,却承载着特殊意义:它是人类天生渴望的互动与联结的入口。
如今寒暄不再令我焦虑。我不再纠结完美表现,而是自主选择社交方式。这一个月的突破让我看清:我们都在遵循相似脚本建立共识,但这不妨碍重写脚本,让对话更真实有趣。
(后接新闻通讯订阅及常见问答部分,此处按用户要求保留原文格式未作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