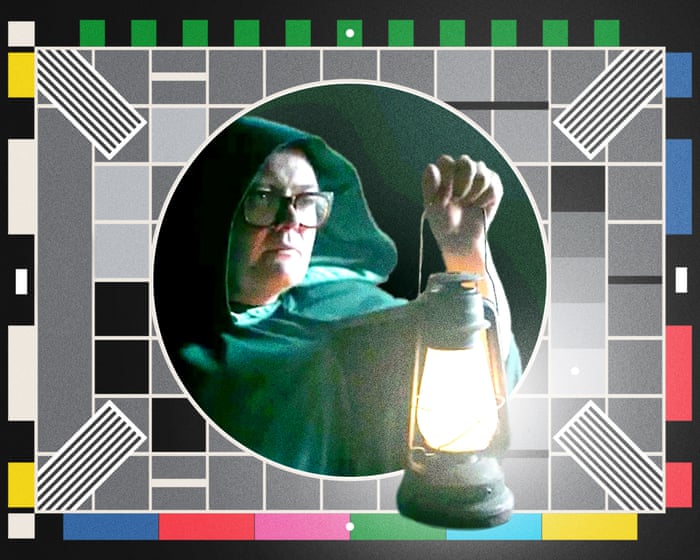当一位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记者与一位前政治家齐聚探讨世界现状与未来,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专攻中世纪史与军事史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以《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及新作《联结:从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信息网络简史》等宏阔著作闻名;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裔美籍记者玛丽亚·瑞萨,是新闻网站Rappler的联合创始人;英国学者罗里·斯图尔特则是前保守党议员、作家及播客《其余都是政治》的主持人。这场对话触及人工智能的崛起、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甚至调侃了“特朗普与普京举行婚礼”的荒诞设想,但始于一个贯穿他们工作的核心命题:在日益分裂脆弱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追求良善生活?
赫拉利指出,人类对此已争论数千年。现代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键智慧在于“求同存异”——承认人们对良善生活存在不同理解,但仍能在基本规则下共存。问题在于,那些自认掌握唯一真理者总试图强加于人。许多意识形态都包含这样的信念:让所有人遵循同一道路是良善生活的组成部分。可悲的是,强加理想往往比亲身实践更容易。他举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为例:难以践行谦卑、慈悲等基督教价值观的人们,却不远千里以这些原则之名杀戮异族。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正重演类似剧本。
斯图尔特反思道,这一切的核心是自由主义——这个19世纪壮大的思想在二战后重获新生。我们继承的体系建立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国家间协定以及强调宽容与人权的民主制度之上,旨在保护少数群体免受多数压迫。尤其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之前,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方向。但此后体系开始瓦解:威权民粹主义取代民主,保护主义与关税壁垒取代自由贸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取代规则秩序。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更放大了这些趋势。
瑞萨补充说,当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规则秩序双双失效,当前紧迫议题在于“有罪不罚”是否会成为常态。当科技巨头为牟利而监控操控我们时,何谈良善生活?如今技术已能精准靶向每个民主国家的个体,直至细胞层面。她指出世界五大宗教的共同教诲:追求良善生活的本质是内心斗争——更好的自我与最糟的自我博弈。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般简单的黄金法则,但当联结方式本身已被腐蚀,我们该如何坚守这些价值?
赫拉利强调,当今新技术允许我们“入侵”人类并操控内心斗争,这是中世纪甚至20世纪无法想象的。掌握此力的巨头集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解码并塑造人类欲望与思想。18-19世纪设计的自由民主制度尚不知如何应对。
斯图尔特提出技术凌驾人类的风险。文明长期建立在推动人性边界的伟人英雄之上,我们以科学、诗歌、戏剧等独有成就为傲。但通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超人类”——若它能毫不费力写出更优诗剧,人类存在的意义便遭消解。
瑞萨指出驱动变革的技术远非精确。成长于信息可信环境的我们易受欺骗——眼见文字即信以为真。人工智能的落地常与事实脱节。赫拉利在著作中强调信息不仅是事实,更是我们讲述的故事,但事实才是共同现实的锚点。
她向众人发问:“各位认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听起来带有宗教色彩,却至关重要。”公共信息生态的崩溃与民主选举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的现象,部分源于对人性良善的消音。她曾在战乱地带见证人类相残,也在灾后现场目睹惊人善举。若非民众对Rappler倾力捐助,菲律宾无法挺过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六年执政——这正是攸关存亡的较量。
赫拉利提出关键洞见:良善与智力并无强关联。人工智能虽是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但我们忘了智力无法保证良善或智慧。历史上从无证据表明智力与慈悲相关,甚至与认知现实的能力无关。人类是地球最聪明的物种,却也是最易自欺的——相信黑猩猩、大象或老鼠绝不会相信的妄念。如今我们创造着超级智能,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可能陷入超级妄想。
斯图尔特称赫拉利的罕见之处在于能预见两百年后的世界。但聚焦未来二十年:硅谷视角常幻想《星际迷航》式未来与马斯克的火星殖民,然而全球约半数人口——数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数十亿人不足5美元。冲突形态也在演变:加沙与乌克兰战事显示,富裕技术强国能对邻国造成巨大伤害而自身风险极小。同时全球军备竞赛加速——欧洲防务开支将达GDP的5%,这意味着本就停滞的老龄化经济体每年从医疗、教育、福利体系抽走数千亿欧元。未来10-20年随着AI发展,世界多数地区或将沦为更破败贫困的版本,收入中位数停滞,冲突加剧。
瑞萨坦言比斯图尔特更悲观:“我认为无需二十年。菲律宾年均遭遇20场台风,岛屿正在消失,而西方仍在争论气候变化真伪。新闻业将在半年至一年内崩溃——网络环境日益恶化且毫无保障,新闻机构被迫承担成本而内容遭掠夺。这种掠夺性网络生态已蔓延至现实世界。”
赫拉利总结道,若要以情感基调形容多年工作,自己始终在传播焦虑——关于AI、气候变化等议题。现在必须转向重建信任:当焦虑泛滥而信任缺失时,万事难成。关键在于恢复对媒体、政府等人类机构的信心,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
斯图尔特认为重建信任意味着修复人类机构。作为前政客,他目睹政府比想象中更糟糕——曾任英国首相的同事利兹·特拉斯将职责简化为Instagram运营与竞选活动,极少关注政策实效,整个体系已沦为游戏。
瑞萨诘问:“在世界分崩离析时,我们还能假装选举公平多久?”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曾有效运转,因有追求更善社会的强大锚点——我们期待领袖克制贪欲,记者实施监督。如今美国若只关注自身,是否意味该抛弃国际组织的嵌入价值?若最强权者仅谋私利,是否将陷入人人自危?
赫拉利指出君主制思想的诡异回归。当今崛起领袖不同于20世纪独裁者:美国“反对帝王”运动针对特朗普并非偶然——他在复活某种中世纪观念。去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时惊人表态显露其政治观非关国家民族互动,而是个人、君主与王朝往来。当人们指出普京屡毁协议时,特朗普回应“他毁的是与拜登、奥巴马的协议,与我的无关”,暗示协议存于个人之间,若他与普京缔约必保履行——但仅限其任内。这使政治重返家族王朝事务。若设想乌克兰战争以巴伦·特朗普迎娶普京孙女并获得克里米亚与顿巴斯作领土的方案,听来荒诞却非完全不可能。
他补充道:20世纪独裁者受意识形态约束,例如共产主义独裁者必须推进理想而不能随心所欲。而特朗普等现代领袖毫无意识形态束缚,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等人同样享有惊人行动自由。
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我们失去了与领导者交涉的道德语言。特朗普本质是无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文艺复兴政治理论家甚至美国制宪先贤都难以构想如此无视宪法、少数群体、真理并公然标榜不道德的行径。更难以理解我们何以沦至近乎“娱乐化”围观曾令我们深感不安的日常言行。
当泽连斯基访白宫时,媒体报道仅复述特朗普谎言而未加质疑,这令人震惊。其实应采用“真相三明治”策略:先陈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实,再报道特朗普的虚假指控,最后重申真相。新闻业必须进化,不能再以“双方各执一词”的中立报道为掩护,必须揭露谎言因其违背事实。我们的报道方式亟需改变。
技术上,我们不能接受监控牟利或持续被操纵,因这会诱发人性之恶。Rappler两年前开始开发聊天应用,旨在建立植根社区的全域信息生态。这正是进步之道:拥抱技术、批判缺陷、以史为鉴,并认知尽管问题重重,民主仍是我们最好的制度。或许一切即将崩塌,但我们持续抗争。
更多人需明白必须亲力承担艰难任务。常有人假设现实自会纠正谬误与非理性政策,但历史从不如此运作。若要让真理与现实胜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付出努力——择一事业专注深耕,并相信他人各司其职。这能帮助我们免于陷入绝望。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是与尤瓦尔·赫拉利、罗里·斯图尔特、玛丽亚·瑞萨等思想家对话后,关于在挑战时代追求良善生活的常见问题集锦:
核心理念与定义
问1:在困境中“追求良善生活”究竟指什么?
意指即便面临不确定性、恐惧或社会问题,仍能找到目标、意义与幸福感。这不是回避艰难,而是学习以韧性与正直穿越困境。
问2:为何此议题当下尤为重要?
我们身处技术剧变、政治极化与全球危机并存的时代,这些挑战易使人产生无力感与焦虑,让追求良善生活更显艰难与紧迫。
问3:幸福与良善生活有何区别?
幸福常是短暂情绪,良善生活则更深刻——关乎依循价值观生活、为超越自我的事业贡献力量,并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稳定。
发言者洞见
问4:尤瓦尔·赫拉利对谬误时代探寻真理有何见解?
他强调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取决于对基本事实的共识,建议必须培养批判性思维,警惕印证偏见的信息,因谬误是实现良性社会与良善生活的主要障碍。
问5:罗里·斯图尔特的政治经历如何影响其行动观?
基于复杂现实工作经验,他指出宏大意识形态常会失败,倡导务实的地方性行动——良善生活源于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并做出具体贡献,而非沉溺于抽象网络争论。
问6:玛丽亚·瑞萨对应对恐惧与网络攻击有何建议?
这位频遭攻击的记者提出关键建议:建立坚实支持网络,永不言弃真相。她证明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尽管恐惧仍坚守价值观行动。守护心理空间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与挑战
问7:感到 overwhelmed 且无力时,如何发挥作用?
这是普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