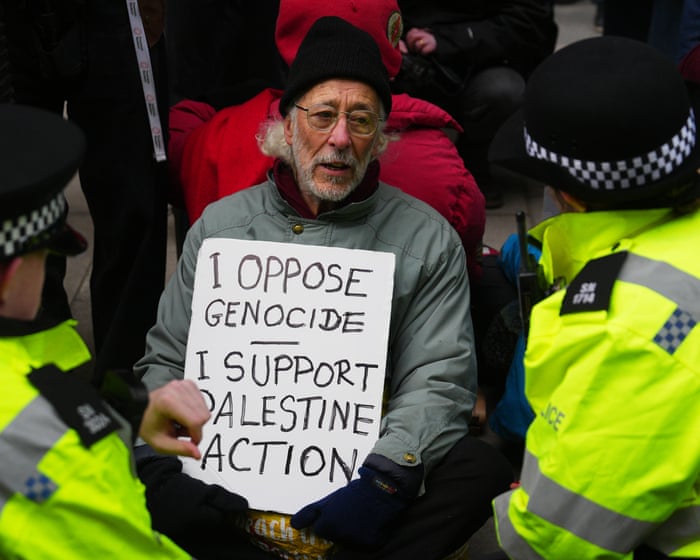我正躺在寄宿学校的床上听收音机,室友在换衣服准备出门。她离开时说:“早餐时见——别迟到。”我刚要起床,早间新闻开始了,我听到播音员念出了我父母的名字。
等室友到达餐厅时,所有人都已得知消息。朋友们跑来陪我。舍监夫妇站在我的卧室外,不让任何人进去。他们只能听见我的尖叫和家具碎裂的声音。这一切令人无法理解,而从那一刻起,所有事情都将如此。
1978年五月那个阳光明媚的银行假日,我的母亲、父亲和妹妹乘直升机前往法国勒图凯吃午餐——这条航线父亲曾飞过无数次。返程途中,英吉利海峡上空的空中交通管制失去了联系。他们再未进入英国领空,被推定遇难。
几周前,我和一位朋友曾把床单系在一起,爬出卧室窗户与男友会合,在伦敦过夜。女生负责人举报了我们,但由于没有证据,我们矢口否认,躲过了开除处分。
如果当时我被开除,我就会和父母在一起——也就不会活到今天。
听到噩耗后,我的记忆变成了连环画——一帧帧无声的画面。卧室门开了,姑姑邦妮(父亲的姐姐)走了进来。我坐进父亲的车。司机艾萨克——我从小敬爱的人——穿着笔挺的西装系着领带,坐在驾驶座上失声痛哭。朋友们围在车边哭泣拥抱。车缓缓驶离,一切仿佛慢动作。我盯着窗外那些凝视我的面孔,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前往赫特福德郡哈彭登老家车程不到一小时。我独自坐在后排——姑姑全程没有触碰我,也没有说话。途中我只记得皮革的气味、艾萨克的啜泣和他须后水的味道。
到家时,我的两个姐姐——19岁的路易丝和6岁的索菲——已在屋里。直升机上的艾玛当时14岁,我16岁。房子里挤满陌生人,电话响个不停,人们进进出出,含泪追问:“女孩们在哪里?医生来给她们开镇静剂了吗?”我感觉自己像踩在高空钢丝上——不敢动弹不敢说话,只能竭力保持平衡以免坠落。
有段时间来了两名警察。我盯着他们闪亮的皮鞋和紧绷的制服,不明白他们为何出现在这片混乱中。
那天的记忆自此空白。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和谁说过话。始终没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只从新闻里知晓一切。
那晚,路易丝和我睡在父母的床上。以前父亲出差时,我常溜到母亲身边,她会说:“哦不行,你不能睡这儿。”我就回答:“好吧,那我陪你看电视再回自己床。”结果总是睡着。
此刻我躺在父亲那侧彻夜未眠。我盯着衣帽间里他整齐排列的皮鞋,想象他穿每双鞋的样子,猜测他会配什么袜子。他的鞋保养得极好,都用鞋楦撑着。我幻想自己缩得足够小,能睡在某只鞋里。
父亲经营植物租赁和土方工程公司,曾参与布里斯托尔附近M5高速公路建设。后来他卖掉公司投资其他项目。和母亲一样,他总是衣着考究。我曾看他擦鞋——手伸进鞋里转动着上油,再抛光至锃亮。皮革被擦得闪闪发光。
随后数日,英法军方展开大规模海空搜索。至今无人知晓事故原因。当日出海的渔民都说天气晴朗无雾。
离家前,父亲最后一个电话是确认直升机的水上浮筒(用于水面降落)是否正常。浮筒完好。这让我相信直升机仍在海峡漂浮,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路易丝和我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母亲的头发被海水打湿塌掉,她肯定会抱怨。他们很快就会回家——父亲穿着皮鞋,母亲做好新发型,艾玛和我会继续玩耍。
事故几天后,我在父亲书房打开抽屉,发现他夏天常戴的金鱼吊坠项链——原以为早就丢了。我们在葡萄牙度假时,他会穿喇叭牛仔裤、牛仔夹克敞着怀,配上这条金鱼项链。在七十年代,这是很酷的打扮。我抓起项链冲进走廊大喊:“爸爸,我找到你的项链了!”照顾特殊需求妹妹索菲的互惠生惊恐地看着我。
家里有间“泳池房”俯瞰肾形泳池,配有高级音响系统,装饰着橙色灯芯绒矮沙发、软木墙和磨砂镜。夏天音乐总是震天响——通常是海滩男孩或大卫·鲍伊。滑动玻璃门通向泳池,那里总是挤满朋友。母亲常穿着淡粉色碎花比基尼、软木坡跟鞋,戴着大草帽坐在人群中。索菲也在,从池边跳进我朋友的怀抱。
两周后,现实降临。父亲的遗体在法国海滩被发现。又两周后找到母亲,再两周后发现了仍系在座椅上的艾玛。我明白这与潮汐有关。
找到父亲时我独自在家。电话响起,邦妮说:“找到你父亲了。”我尖叫:“他在哪?”她回答:“不,菲奥娜,他死了。”
搬离前的四个月记忆模糊。我们在哈彭登举行了三场葬礼和一场追思会。当地店铺为此歇业,我穿了母亲的一套衣服,心想她知道定会生气——她非常时尚,衣服都是高级定制,精致美丽如她本人。追思会上我突然不可抑制地大笑不止,那是我第一次彻底失控。路易丝、艾玛和我曾就读的预备学校来了些女孩,戴着红丝带装饰的米色草帽和鲜红色羊毛外套。
毫无预兆地,人们开始打包我们的家。我走进厨房,看见搬家公司的女工正在清空橱柜——没有男性,全是老年妇女。一个系着厚围裙的女人看着我说:“我们会非常小心。”她手里拿着父亲的水晶平底杯。
大约五岁时,我有个固定仪式:父亲下班回家,我会推椅子到酒柜前,取瓶子给他调威士忌兑水。他会捏着我的拇指,在指关节上方比划该倒多少酒。递过酒杯后,我就爬上他的膝盖,头贴着他胸膛,听威士忌在他体内流动,像小小的波浪。
我想现在人们都怕我。我盯着他们,几乎不说话。感官变得异常敏锐,感觉自己更像动物而非人类。
事故几天后,邦妮来家里打开保险箱拿走了里面的东西,包括母亲的一些珠宝。母亲酷爱珠宝,父亲也热衷为她购买。她进房间前总能听见金饰手链的叮当声——那条链子挂着26个吊坠,每个都是父亲为纪念共同生活的时刻所赠:威尼斯蜜月的贡多拉、首次滑雪假期的滑雪兔、幸运如愿骨、四个女儿的专属吊坠,还有象征自由与灵魂超越的飞马。
父亲收藏了大量葡萄酒。姑姑提出代为保管,我和两个朋友花了一整天将酒箱运到她家。某晚我去时,见她从酒架取下两瓶酒。我说:“邦妮姑姑,那是爸爸的。”她回答:“你父母死了。”随即离开。我盯着门,宁愿她用酒瓶砸我,也不愿听到那句话。
祖父母在葡萄牙普拉亚达卢斯有栋房子。祖母是澳大利亚人,觉得这里很像故乡。六十年代时,这里还是宁静渔村,游客稀少。建筑多是粉刷白墙的简朴房屋,当地人骑驴或坐骡拉木车出行。渔民构成社区支柱,决定着舒缓的生活节奏。沙丁鱼、鲭鱼和章鱼在明火上烤作午餐,我们常和他们共餐。吃剩的沙丁鱼尾堆在盘子里计数付钱。我和妹妹艾玛会吃掉整条鱼,在沙地上划线记录吃了多少。
父母爱上这里,在祖父母隔壁买了房,我们每年在此度暑假。
事故几周后,我和姐姐路易丝带着两个朋友飞抵此处。这是个错误。母亲卧室有个上锁的大橱柜,存放所有私人物品,还有防晒霜、帽子、炉甘石洗剂和药箱。她从英国带来各种药品——当地医生稀少,抗生素难求。我们到达时,橱柜已空。
父母所有衣物都不见了,存放钓鱼、滑水、划船设备的室外小屋也被清空。父亲、艾玛和我曾在那里度过无数时光——那是我们的洞穴。钓鱼归来,我们会冲洗钓竿上的盐水,靠墙晾放。
我跑到祖父母的旧宅(现归邦妮所有)。祖父母已故,但当地善良的玛丽亚和若昂夫妇曾照顾他们并维护房屋花园。玛丽亚教我们葡萄牙语,烹制当地菜肴。她含泪开门紧紧拥抱我。我告诉她:“玛丽亚,所有东西都不见了。”邦妮拿走了全部物品,并警告玛丽亚若让我进屋就解雇她。
四个月后,我在剑桥参加一年制住校文秘课程。老家房子已出售。邦妮坚持要我返校,但我无法忍受回去——那里充满不堪回首的记忆。无人知道如何安置我,文秘学院似乎是唯一选择。
我住的是一栋维多利亚式大宅,由一位老妇人和她当医生的丈夫管理。十二个女孩住在这里合住卧室。作为第十三人,我独居阁楼单间。房间没有窗帘,地板裸露。我没有家居 comforts,也不想要——我渴望赤裸独卧在喜马拉雅山脉,那才能给我慰藉。
我想人们害怕我。我专注凝视他们,几乎不开口。感官变得敏锐,自觉更像动物而非人类。仅凭肢体语言就能读懂他人。当人们对我说话时,我想闭眼捂耳。唯一能忍受的声音来自父母和妹妹艾玛。
周末我去伦敦见朋友。和他们相处能帮我理解世界,尽管我无法诉说发生的事或自己的感受。最近我对一位朋友说:“那时我一定很古怪,你们却对我那么好。”她温柔回答:“哦菲奥娜,你不古怪——只是从不说话。”若有人提及父母或妹妹,我就离开房间。
我们外出共度时光。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朋克摇滚乐手。我帮她准备——用蛋清固定刺猬头,穿上豹纹连体衣,涂深色口红化浓妆——然后我们走在国王路上。她享受众人注目,非常美丽。我从不盛装打扮,不愿被注意。
剑桥的一年匆匆而过。唯一与我产生联结的是打字机。我爱桌上那台重金属机器的一切。按键敲击纸张的响亮“咔嗒”声意味着我不必说话,只需咔嗒作响。
离开剑桥后,我和另外五个女孩合租国王路附近的两居室。那是段欢乐时光,派对、毒品、酒精不断。但只要碰触这些,就会引发突如其来的剧烈痛苦。我像张吸墨纸——小小一滴就能浸透每个角落。
我从事秘书工作,这很适合。可以躲在打字机后,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后来我开始出现所谓的“发作”。人们会说:“菲奥娜又发作了。”前兆是颈后汗毛倒竖,头皮发麻。接着我会尖叫、砸东西、逃跑。通常由简单问题触发,比如“你父母住哪儿?”或“你有几个姐妹?”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能杀人。
丈夫说我们初遇时这经常发生。他会花几小时开车在伦敦找我。有次发现我赤脚跑在伯爵宫路上。追上我后他说:“菲奥娜,你的脚。”我跑过碎玻璃却毫无知觉。
我的应对方式是辞职、登机、消失。第一次我飞往曼谷,与国王路结识的朋友卡拉会合——她正在远东旅行。我们结伴三个月,穿越泰国、菲律宾、尼泊尔、缅甸和印度。我研习佛教,遇见在修行所获得开悟的人,但离开时总是感到更孤独——尤其看到别人找到所求。
我始终无法谈论那件事,甚至对丈夫也如此。他说结婚35年,直到通过我的文字才真正理解我。
我的女儿艾玛——以妹妹命名——曾是记者。她读到我从广播得知死讯时指出,如今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现在有严格规定防止媒体在通知亲属前报道死讯。但1978年尚无这些法律。
邦妮几年前去世。听说临终前她想见我。我本愿相见,但为时已晚。她是位高大俊美的女性,颧骨高耸,蓝绿色眼睛引人注目。父亲与她的关系复杂。母亲深爱父亲,但邦妮与母亲关系紧张。我想她未曾得到太多关爱。他们的父亲强势却疏于照料。祖母——他们的母亲——姑姑曾非常疼爱我,我们关系亲密。这对她想必不易。
数十年来,我以为风趣善良的父亲是被一群青少年杀害。三十年后才得知真相。
我也猜想她是否过着1970年代对女性的期待生活——婚姻、母职、家务优先——从未按真实意愿生活。她也深陷悲痛,失去了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支持她的弟弟。我想父亲理解她并给予她大量关爱。我是个倔强直言的孩子,常质疑她的行为。她拿走我们能拿走的一切,是否为了留住父亲的影子?
她成为索菲的监护人。尽管索菲就读威尔士的特殊需求寄宿学校,这仍是重大责任。但这导致更复杂的行为——若索菲行为不端,姑姑常阻止我见她。事故后几个月,有次她扑向我,我们像两只野兽在地上扭打。我跑上楼锁住房门报警,但警察赶到时她已离开。
索菲仍有严重特殊需求,住在寄宿护理院。路易丝和我都住在伦敦,定期见面。无疑共同的创伤影响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而我始终无法谈论。不知我们是否都意识到,最初那些日子能熬过来全靠彼此。我只想与父母和艾玛团聚,但无法忍受让路易丝和索菲承受更多失去。
人们说时间能治愈,但我不确定。我相信爱能治愈。我极度渴望让爱重回生命,而重新去爱与被爱都是巨大挑战。对失去的恐惧深植于每个细胞。多年来我常想,是否该独居荒野,远离所有人,不再期待幸福。
写到这里时,丈夫正在厨房。我有两个孩子、两个孙辈和一个儿媳。我正在金史密斯学院攻读儿童文学与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放学后,我站在新十字车站月台,仰望横跨车站天桥的阿默舍姆酒馆。巨大的红色霓虹灯闪耀着两个字:“鼓起勇气。”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是关于应对家庭突发创伤性丧失的常见问题列表,以自然共情的语气呈现:
**初级问题**
1. 感到完全麻木和震惊正常吗?
是的,完全正常。震惊和情感麻木是大脑保护你免受创伤全面冲击的方式,这是常见的初始反应。
2. 我吃不下睡不着怎么办?
专注于微小可控的步骤。尝试小口喝水、吃吐司或饼干等清淡食物,即使睡不着也尽量休息。必要时可向医生寻求短期助眠或抗焦虑帮助。
3. 该告诉谁?如何告知?
从一位可信赖的人开始——亲密朋友、其他家庭成员或心灵导师。可以请他们帮忙通知其他人,不必独自打所有电话。
4. 如何处理葬礼和法律事务?
寻求帮助。指定一位务实的朋友或亲属协调殡仪馆事宜,或聘请律师指导必要法律程序。没人指望你独自处理这些。
5. 我会永远哭不停吗?
强烈持续的悲伤浪潮最终会减少频率,虽然仍可能意外袭来。哭泣是必要的释放,不是软弱的表现。
**中级问题**
6. 为什么我感到愤怒甚至内疚?
愤怒是悲伤的正常组成部分。内疚常源于“如果当初”的念头,这是试图理解无解之事的痛苦但常见方式。
7. 当人们说“需要什么就告诉我”时,我该提什么要求?
具体说明。可以请求:“周二能带些 groceries 吗?”或“能帮我遛狗吗?”或“请代接保险公司电话”。人们想帮忙但常不知如何着手。
8. 暂时避开逝者房间或物品可以吗?
可以。没有正确的时间表。做你能承受的事。可以把东西装箱以后处理,或请他人打包物品,等你准备好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