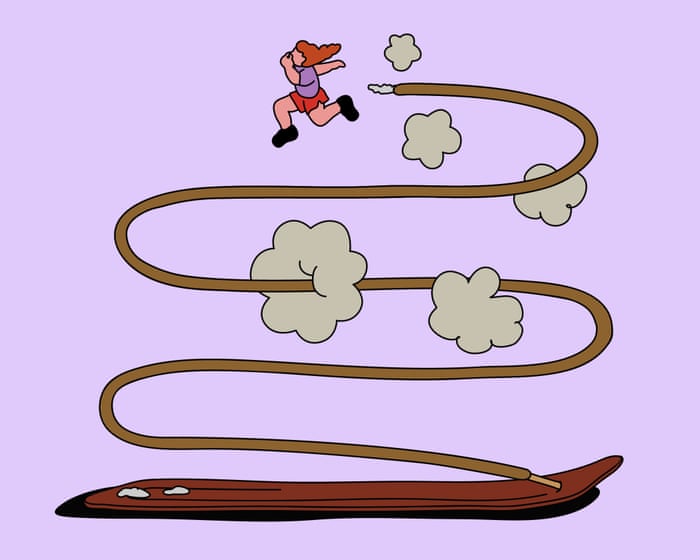在我成长的家庭里,任何德国事物都被禁止。厨房里没有西门子洗碗机或克鲁伯斯咖啡机,车道上没有大众、奥迪或奔驰。这条规矩源于我的母亲。她并非大屠杀幸存者,却始终感受到浩劫的阴影笼罩。1945年3月27日那天,她年仅八岁,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最后一枚击中伦敦的德国V-2火箭夺去生命。那枚炸弹摧毁了东区部分区域,造成134人死亡——其中几乎全是犹太人。这场爆炸的冲击以各种方式塑造了我母亲的余生,也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
她明白这枚炸弹并非特意瞄准休斯庄园,但她更清楚纳粹会对这个结果多么满意——命运或偶然选择了让众多犹太人殒命的地点。在那个三月的清晨七点二十一分,最终六百万的死亡数字又添了一百二十人。于是这条家规诞生:任何德国痕迹不得触及我们的家庭。没有探访、没有度假、没有接触。在她眼中,德国是个有罪的国家,每个国民都与二十世纪最恶劣的罪行脱不开干系。
我认识的其他犹太家庭也有类似规矩,但很少像我母亲这般严格。不过她的深层信念并不罕见——许多犹太社区内外的人过去乃至现在都认同我自幼被灌输的观念:除了少数例外,阿道夫·希特勒在德意志民族中找到了心甘情愿的同谋。
我们常听闻法国抵抗运动和欧洲各地的地下斗争,却很少了解德国本土的反抗。许多人认为异见者在1933年纳粹掌权后迅速被肃清:"他们首先抓走了共产党人……"但这并不完全准确。有些德国人从最初就反抗第三帝国,并持续抗争至其统治终结。战后一位盟军调查员估计,有三百万德国人因异议行为进出监狱或集中营——有时仅因一句批评就遭惩处。
他们传递禁忌信息,低声谋划,梦想着没有元首统治的未来。
1933年,德国有六千七百七十万公民。超过95%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儿童)唯命是从,行礼高呼"希特勒万岁!"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挺身而出?当众人皆顺从时,是什么让人选择拒绝?当沉默如此容易而反抗只会带来痛苦、艰辛或死亡时,为何要冒此风险?
任何仔细审视二十世纪中叶恐怖历史的人都可能追问这些问题,尤其是一个:若我在当时会如何行动?我们多数人愿意相信自己会勇敢地成为反抗者,但数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大多会选择沉默。
三年多前,我偶然发现柏林上流社会一个群体的故事,他们属于那个罕见的类别:拒绝向希特勒低头。这段除少数专家外已被遗忘的往事充满了骇人的残酷,但其核心却存在着同样难以解释的东西——激进、不必要且致命危险的善行。
故事还有转折。这些卓越的个体大多通过独自行动反抗政权......救援与抵抗行动都是秘密进行,从未公开讨论。但在某个决定命运——最终致命——的日子,他们汇聚到了一起。
表面上,这是一场庆祝朋友生日的茶会。实际上,这是交换禁忌信息、分享秘密计划、谋划没有元首统治之未来的机会。那天下午,他们在同志情谊中寻求慰藉,为得知自己并非孤军奋战而松了口气。然而正是这次聚会导致了他们的覆灭,因为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威胁——来自内部的背叛。
他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一群更习惯歌剧院之夜和大使馆派对的柏林精英,如何卷入这场即将变得致命的戏剧——其后果将触及纳粹国家最高层的戏剧?那些本可轻易保持沉默、远离麻烦的人,为何选择赌上一切?
他们的反抗之路既不平坦也不直接。每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做出决定,往往通过曲折迂回的路径。对有些人而言,这甚至不是选择——而是对周围日益黑暗的世界唯一可能的回应。这些问题在1930至1940年代的德国显得尤为沉重,但并不局限于那个时代或地点。有些回响穿越数十年,有些在今日仍产生强烈共鸣。
要理解这个群体的非凡人物,不妨从玛丽亚·海伦娜·弗朗索瓦丝·伊莎贝尔·冯·马尔特扎恩——瓦滕贝格和彭茨林女伯爵——开始,从1943年秋天盖世太保敲响她家门的那天说起。
玛丽亚当时仅34岁。此刻武装人员正涌入她的住宅,搜寻他们确信她藏匿的犹太人。巧合的是,就在她站立的房间内,正藏着一位屏息凝神的犹太人。但她拒绝流露丝毫恐惧。从先前与秘密警察的交手中,她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课:自信就是一切。关键是展现出不可动摇的沉着。
藏匿者是她的恋人汉斯·希尔舍。他们为这一刻准备了超过18个月。汉斯搬来时带来了一张厚重的红木沙发床,其底座足以容纳一人躺卧。靠垫归位后,开口便无迹可寻。玛丽亚加装了挂钩和孔眼,让内部的人能反锁机关,使外部无法打开。
汉斯曾担心窒息,于是玛丽亚用手钻打出气孔,并从内侧覆以与沙发同色的红布。她每日在内部放置一杯水和足够剂量的可待因——用以抑制他可能暴露行踪的持续咳嗽。这个藏身处始终处于待命状态,以备不时之需。
此刻危机已然降临。汉斯藏身其中,竭力保持寂静,而两名盖世太保正在公寓里翻天覆地。
他听见了他们的动静。几小时前警告就已传来:大楼门房悄悄塞给玛丽亚一张留在走廊的黄色索引卡。仅五个单词——其中一个甚至不是真词——却足以意味死刑判决:
"马尔特扎恩家有'J'!"
(注:J为Jew/犹太人缩写)
这种告密在当时的柏林司空见惯,邻居间互相指控藏匿犹太人。窥探的目光无处不在,搜寻着雅利安人将谁藏在阁楼或地下室的任何迹象。有时被告甚至会变成告密者——以此转移嫌疑并讨好秘密警察。汉斯和玛丽亚确信警察已经到来。写纸条的女子(显然被盖世太保官员误放了纸条)早已受到怀疑。因此敲门声响起时,他们并不意外。
玛丽亚开门面对两名要求入内的男子。她拖延了足够时间让汉斯溜进卧室,无声地爬入床垫下的空洞平躺。此时是下午两点三十分。
盖世太保行动迅速,拉出抽屉,撕开橱柜。很快他们发现一排男式西装并质询玛丽亚。她说了部分实话:去年九月她生下一个男婴,"我向您保证,这孩子不是圣灵所孕"。直到此时她才撒谎,称孩子生父不是汉斯,而是同性恋朋友埃里克·斯文森——他曾假扮她的情人。
搜查持续着。藏在箱内的汉斯能听见地板上的脚步声。玛丽亚正在给两只狗抛球玩耍。盖世太保明显恼火地命令她停止,但她拒绝并解释这是狗每天下午散步的常规时间,"它们需要运动"。
三点钟过去,四点钟过去,审问仍在继续。"我们知道有个犹太女孩在你公寓住过两周",他们确信没有漏过任何线索。
"我确实雇过个女孩,但她不是犹太人",玛丽亚回答,"她的文件完全合规。"
"不,那是伪造的",一人坚持道。
玛丽亚反问自己区区一个兽医学生怎会懂这些,装作对这个想法震惊不已。
此时他们进入卧室。正式审讯开始,汉斯能听见三个人的声音。男子命令玛丽亚坐下,她缓缓落座于沙发床上。
"我们知道你藏了犹太人",他们说。
"这简直荒谬至极",玛丽亚竭尽所能摆出傲慢姿态回答。就在她身下几英寸处,汉斯一动不动地躺着。
她指向房间里最显眼的位置——她父亲身着礼服的贵族肖像。"您不会相信,作为这个人的女儿,我会藏匿犹太人。"
汉斯保持僵硬姿态,聆听着每个字。然后他恐惧的时刻来临了。
盖世太保坚持要玛丽亚打开房间里的两张沙发床。汉斯听见她轻松打开第一张,无疑还夸张地展示空荡内部,仿佛在暗示探员们浪费时间。
他们转向第二张——他的藏身之处。他能感觉到动静,感觉到掀盖的努力。
"抱歉,打不开",玛丽亚说。她解释买来后不久就试图打开,但卡住了。男人们不信,用力拉扯决心强行打开。
接着玛丽亚赌了一把——这需要钢铁般的自控力。汉斯听见她的话却无法反应,因为她向盖世太保提议:
"掏出你们的枪射穿沙发。"
她听起来极其严肃,仿佛在给僵局提供合理解决方案。"如果你们不信我,只需掏枪射穿沙发。"
汉斯躺了多久等待纳粹的回应?玛丽亚的话语在空中悬停了多久让他绷紧神经?他们中任何人掏出手枪揭穿她的虚张声势只需一秒。若他们开枪,汉斯需要多久会死?几秒?一分钟?
是否此刻正有人——他将武器瞄准床箱,枪管仅几英寸远。然后玛丽亚再次开口。
"但是",她说。她有一个条件:若他们开火,必须提供新装饰面料的欠条并支付维修费用。她态度坚决——家中不能有"破烂家具"。"我要你们提前书面保证。"
与各类国家社会主义官员打交道近十年后,玛丽亚还学到一点:这类人害怕越权。需要填写费用报表,需要向上级交代。果然,子弹留在了枪膛中。
到六点钟,盖世太保终于离开。他们在公寓里待了将近四小时,只带着女伯爵的承诺空手而归:如果那个犹太女孩再次出现,她会立即上报。
直到确信那些人彻底离开后,玛丽亚才示意汉斯打开藏身处出来。他现身时面色死白,浑身冷汗,确信那漫长的几小时可能是他最后的时光。救他的是被他称为玛鲁斯卡的女子的不可动摇的自信。尽管她如今作为见习兽医住在柏林废弃店铺里,但她出身于统治这片土地数百年的阶级。就连盖世太保也无法恐吓她——至少此刻还不能。
奥托·基普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这较少源于他的社交魅力或其年轻妻子的魅力,更多因为他作为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位。请柬每日纷至沓来,但有一封格外醒目:为致敬世界上最受敬仰的人物之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而举办的晚宴。
定于1933年3月中旬的这场活动,策划于数月前,远在纳粹于一月底夺取政权之前。最初邀请德国在纽约的官方代表只是礼节之举——爱因斯坦毕竟是该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当奥托·基普看到桌上的请柬时,其意义已彻底改变。
爱因斯坦此时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象征——一个在转而反对自己犹太人的国家中的犹太人。向他表示敬意的晚宴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声援德国受迫害犹太人的集会,以及对新政纳粹政府的抗议。如果奥托参加,他将与抗议者站在一起。在上司眼中,他将站在敌人一边——成为叛徒。
然而如果他拒绝,他将默许那些在德国和纽约迫害爱因斯坦的人。奥托甚至听闻针对这位科学家的暗杀阴谋: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德国交换生正谋划在爱因斯坦登船返回欧洲前刺杀他。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奥托对形势越发清晰。出席爱因斯坦荣誉晚宴意味着他外交生涯的终结。拒绝则意味着与国家社会主义及其暴力支持者为伍。这就是他面临的选择。
1933年3月16日,爱因斯坦抵达纽约。在被记者包围时,他赞扬"德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如此重要和显著,难以想象没有它的世界"。他补充说更可悲的是"这种文化的真正代表现在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虐待"。关于德国官员公开支持爱因斯坦意味着什么——任何奥托可能找到外交掩护的灰色地带——此刻都已消失。他必须做出决定。
他决心为自己服务并热爱的国家做认为最有益的事。为了德国的声誉和体面,他接受了晚宴邀请。组织者请他发表演讲。
这一次没有犹豫。请求是标准程序——作为在场最高级别的德国官员,预计他应该发言。此外,他认为半途而废没有意义。如果要冒险职业生涯,就要公开而自豪地去做。他开始准备简短演讲。
晚宴是典型的曼哈顿盛会。在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酒店,女士身着礼服,男士穿着白领结燕尾服,弦乐四重奏在宾客入场时演奏。奥托·基普被安排在主桌。
寒暄和正式欢迎后,轮到他发言。在安静的房间里,这一刻的分量显而易见。每个人都知道每个字都至关重要。
他首先赞扬爱因斯坦对科学和人类的贡献。他称赞美国欢迎德国知识分子,然后委婉批评自己政府,说伟大国家对新思想开放,不以其来源评判。
最后他转向爱因斯坦:"这次聚会不是向您致敬,爱因斯坦教授。相反,是您荣耀了这次聚会——以及您选择加入的任何聚会。"
掌声经久不息且发自内心。当活动登上次日《纽约时报》头版时,很少有人惊讶。奥托对很快出现在柏林纳粹党报上的报道同样不意外,该报指控一名德国官员在满是犹太人的房间里侮辱第三帝国。不久后,他被命令返回德国"接受问询"。 among those he would have to answer to was Germany’s new chancellor: Adolf Hitler.
伊丽莎白·冯·塔登作为德国精英女儿们的女校长,最初以开放心态接近纳粹主义。但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很快变得无法忽视。首先,一些她最钦佩的女性因为犹太身份失去职位,不得不关闭机构。
接着,伊丽莎白明白了第三帝国对基督教的意图——旨在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教会",作为全能纳粹国家的延伸,将阿道夫·希特勒提升至耶稣基督之上。到1934年11月,她已与持异议的认信教会结盟。
很快,她发现自己陷入两种冲突力量之间。一方面,她对国家方向深感厌恶,希望忠于信念。另一方面,她需要保持几年前在维布林根创办的学校运营,该学校已迅速在德国许多领导家族中赢得良好声誉。
为此,她谨慎选择斗争。她容忍了许多认为不可接受的事情,并在可能处找到聪明妥协。例如,她允许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女子分支——德国少女联盟——但确保由学校自己的教师而非外部纳粹官员监督。通过这种方式,她希望控制和限制在自己屋檐下发生的灌输。
伊丽莎白遵守当局要求的任何事项,例如在学校入口展示纳粹党纲,只为维持机构运行。她相信没有学校,她无法传递珍视的社会责任和基督教虔诚价值观。更实际的是,没有学校,她无法为需要帮助的女孩提供庇护——这种需求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quietly,伊丽莎白一直在接收"非雅利安"背景的学生。学生们注意到新女孩突然在学年中途到来,很快又消失。可能解释是这些女孩在学校停留,而她们家人获取逃离国家所需文件。
1936年,随着国家对教派学校和基督教的敌意加剧——纳粹党越来越推广想象的日耳曼异教历史——她谨慎地从校名中移除"福音"一词。但在更名的乡村女子教育之家内,教职工和学生都不需使用"德国问候语";没有希特勒敬礼。
她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使她刚好在帝国正确的一边,允许她 subtly抵抗。这种平衡一直保持到她犯错那天。讽刺的是,导致她垮台的正是她心爱圣经中的一段话。
事件发生在1940年6月庆祝德国战胜法国的学校仪式上。伊丽莎白朗读了一首赞美诗。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一个学生正密切关注——不是出于宗教兴趣,而是因为她是个间谍。
这种情况源于伊丽莎白在原则与保持与德国新统治者文明关系的实际需要之间走的谨慎路线。那年夏天,在她50岁生日庆祝会上,客人包括一名犹太女性——原名为玛戈特·科恩的天主教皈依者——和纳粹妇女协会当地领导人玛莎·赖希林·冯·梅尔德格男爵夫人。邀请男爵夫人似乎是谨慎的外交举动,以安抚当地著名纳粹支持者。
问题是,男爵夫人的热情延伸至鼓励她13岁的女儿在学校内充当秘密线人,监视一切。她向母亲报告所见所闻中任何偏离纳粹信仰的内容,母亲随后向当局报告这些"信念缺陷"。不久后,一封官方信函抵达。政权得知塔登小姐在纪念德国人民的仪式上朗读了《旧约》。通过包含犹太经文,她玷污了国家场合。盖世太保派出一名检查员。
他发现许多违规行为。学生没有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问候。在朗读希伯来赞美诗的同一胜利仪式上,关于元首只字未提。他的肖像也没有展示。
最终做出了决定。伊丽莎白的国家许可被吊销,她奉献的学校因"未能为年轻人提供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足够保证"而被关闭。它被一所更名的新中学取代。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工被允许留下,但伊丽莎白被 forced out.
因此,1943年9月,失业且失去使命的伊丽莎白·冯·塔登邀请一些朋友喝茶——包括玛丽亚·冯·马尔特扎恩和奥托·基普。受邀的还有前财政部官员、医生、一度是模特的人、高级外交官以及汉娜·索尔夫——一位以在沙龙接待反纳粹异见者而闻名的大使遗孀。这原本 promised to be一个愉快的下午——志同道合灵魂的聚会,他们可以分享信息、纳粹之后未来的计划,以及或许最重要的: reassurance他们并不孤独。
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among them, 喝茶吃蛋糕的人中,有一个他们信任为自己人的人——实际上即将向盖世太保背叛他们所有人。这种欺骗行为将导致纳粹最残忍者之一的追捕、酷刑、一场作秀审判,并最终以断头台和绞索处决。 repercussions甚至将触及阿道夫·希特勒本人。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与背叛、抵抗及其代价的故事。而且这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这些反抗者的勇敢,以及它教导我们关于对抗暴政的一切,直至今日依然 enduring.
这是乔纳森·弗里德兰所著《叛徒圈:反抗纳粹者与背叛他们的间谍》的编辑摘录,由约翰·默里于9月11日出版,定价25英镑。支持《卫报》,请在guardianbookshop.com订购您的副本。
常见问题解答
当然,以下是受上述故事启发关于纳粹时代德国抵抗主题的常见问题列表
基础问题
问:关于贵族和沙发床的故事是什么?
答:这是关于德国贵族兼抵抗战士玛丽亚·冯·马尔特扎恩女伯爵的故事。她在沙发床内建造隐藏隔间,庇护她的犹太恋人汉斯·希尔舍及其他犹太人免受纳粹迫害。
问:那时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吗?
答:不,这是常见误解。虽然许多人支持或顺从政权,但德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以各种方式积极抵抗希特勒的个人和团体。
问:德国抵抗是什么意思?
答:指1933至1945年间德国境内个人和团体对纳粹政权及其政策的公开及秘密反抗。
问:为什么这个故事重要?
答:它突显了普通人冒着一切风险保护他人的非凡勇气,挑战了"德国无人试图阻止纳粹"的观念。
进阶问题
问:除了藏人,抵抗还采取哪些形式?
答